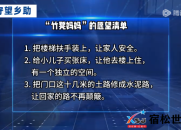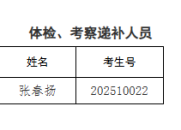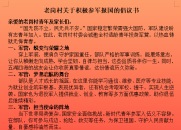|
面对丈夫的悄然离弃,她默默承受,一个人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面对小叔的先天残疾,她不离不弃,既当嫂子又当娘张罗一切。她就是趾凤乡吴河村村民张小玲,用柔弱双肩为家人撑起一片天 3月11日,记者在吴河村计生专干贺轶萍的陪同下,赶到凉亭街一个小型服装厂,数十名缝纫工正埋头制衣,贺轶萍指着一个娴熟剪线头的中年妇女说,她就是张小玲。记者难以想象,就在这个中年妇女娇小的身躯里,竟然蕴藏着无比强大的能量。 “我在厂里做计件工,主要负责剪线头、包装和熨烫衣服,每月平均有1500元左右的收入。厂里没订单时,我就在家闲着。”张小玲说。 1962年,张小玲在河塌乡四利村出生,不到一个月不幸就开始降临,母亲突然患病离世,家人无奈之下,只得把她抱养到趾凤乡一周姓农户家做“童养媳”。 1972年小叔周海兵出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家人发现他先天残疾,左腿行走不便,且说话含糊不清。从此,照顾小叔的生活、送他上学成为年幼的张小玲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 1984年,张小玲与丈夫结婚。第二年,大女儿出生了。丈夫在当地做木工,自己在家务农,一家人到是过得其乐融融。 命运又跟她开了一个玩笑。 1993年丈夫到海南打工,渐渐和家人失去联系。 “1992年婆婆去世家里欠下3000多元的债务,他头三年每年还寄两、三百元钱回家,之后就杳无音讯了。那时没有电话,我就托人写信给海南的熟人让他们帮着打听下落,但一直没有结果。” 上有老,下有小,她深知生活还得继续。为了撑起整个家,家里7口人田地的农活她硬是一个人顶了下来,抽空还要养牛、喂猪,一刻也不得休息。眼见小叔同龄的人都成了家,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四处托人帮小叔张罗亲事,最终在太湖县马庙乡物色到一个姑娘。 1999年正月小叔成家了,她总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 仅在庄稼地里刨食,难以维系一家人的生活。公公去世后,在娘家哥哥的劝说下,她搬到河塌,挑着一担柴火在四利村一个豆腐坊里交学费,学了一晚做豆腐,加上以前在家做过豆腐的经验,她就开始张罗起小豆腐摊了。晚上做豆腐,清早卖豆腐,白天打理近3亩的庄稼地,抽空还帮农户割稻攒钱养家。这一干就是8年。 “当时做豆腐每天能赚7元钱左右,完全不够一家人的开销,我只好再找点别的事干。割稻每亩工钱30元钱,包割包挑每亩可得70元。那几年我真不知道自己怎么挺过来的。”说话间,她的眼睛开始湿润。 2000年,小叔的女儿出生了。由于弟媳生活自理能力差,她不放心小叔一家人,2001年也把他们接到河塌。 “我用箩筐一边装着行李,一边放着孩子,挑着担子,走了7里的山路才坐上车到河塌。当时看见的熟人笑称我为‘牛郎嫂’哩!做豆腐时,弟媳主要负责生柴火,卖豆腐时我都是背着小侄女一起。”张小玲说。眼见嫂子忙里忙外,小叔心里很着急, “这一大家子光靠姐姐一个人不行,把你累坏了,父母在天之灵也不原谅我。”架不住小叔的再三劝说。 2001年,小叔前往浙江一修路工地做小工,之后间断地外出打工赚点小钱。从此,张小玲又多了一份挂念。 2007年,她以每年400元租了3间瓦房,带着小叔一家人搬到凉亭街。卖了一年豆腐,然后到当地一面包厂打工,还抽空种了近2亩的庄稼。眼瞅着小叔的孩子一天天健康长大,她也安心多了。 2010年,在女儿的强烈请求下,她到芜湖帮女儿带小孩。2013年4月份,弟媳因为孩子与旁边一户人家发生口角,并发生肢体冲突,对方突发脑溢血死亡。得知情况后,她立即赶回凉亭,正碰上对方索要赔偿费用,一贫如洗的家庭哪拿得出那么多钱?她只好当地一跪,请求对方的谅解,这一跪感动了在场所有人。事情处理好后,她又留在凉亭找了份工作。张小玲说: “我找熟人在厂里也帮弟媳找了份剪床前拉布的活,每个月也有700元左右的收入。小叔现在在城里做小工。一家人齐出力,日子会过得舒坦些。” 采访中,今年大学毕业的儿子大勇正好来看望张小玲。 “母亲是一个伟大、坚强的女性。这么多年,她过得真不容易,不仅要支撑整个家庭,供我上学,还把叔叔当做自己的孩子,照顾叔叔一家人的生活。但她从来未有过怨言。”大勇眼里噙满了泪水。 “家里还欠亲戚近2万元钱的债哩。趾凤老家只剩下一间半的老屋。平时过年回老家,我们是借住在隔壁一堂哥家里。村里见我们生活困难,今年还帮我们安排了一个低保名额了。”张小玲告诉记者,她唯一的希望就是还清债务,再攒点钱,做几间像样的房子。 “一家人平平安安,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汪俊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