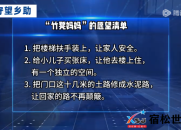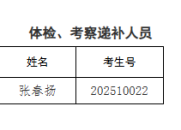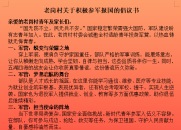|
|
 
引子:送文上门,事出有因,请君判评:文句可顺,层次是否分明?!在《宿松县志》(1978-2002)(以下简称“二轮县志”)主编廖道安的一招狠似一招的追杀下,我只得落荒而逃。但文人的固疾驱使我写出以下文字,算是一个弱者的呻吟吧。效果如何,不存奢望。但肯定会有人怒发冲冠,会有人七窍生烟,会有人拍案而起……我想,最多的还是摇头叹息:为什么想干一点真事的人的处境会如此尴尬?
从一盆铁树谈起
2003年8月26日,临近退休年纪的我象孩童般兴冲冲地来到县志办公室。用点诗意的语言说是来为二轮县志添砖加瓦,发挥余热。能够荣幸地参加二轮县志的编纂工作,令我十分激动。因而全身心地投入,忘我地工作,先是参加筹备业务培训会,而后便四处奔忙征集资料,接着是伏案编撰。
从某种角度讲,县志办公室在经济地位上属弱势部门,原有位于县政府四楼的3间办公室已不够用,在二轮县志编修启动后,于县供销社一楼租了8间办公室,朴素简洁。向来喜欢栽花弄草的我为了美化环境、净化空气,遂于2004年5月自动无偿地搬来几盆花草,分赠给各办公室摆放,走廊上则是一盆铁树,苍劲挺拔,郁郁葱葱,树冠覆盖面足有1.5平米,令人赏心悦目。当然地我又自告奋勇担当起了浇灌侍弄的职责,不到一个月,其枝叶更加茂盛,中心抽出了很多嫩芽,枝条也抽长了许多,枝头自然地挨墙弯曲垂靠,看上去更显风姿绰约,就象一位沉稳而丰满的少妇,让人百看不厌,确实给简洁的办公室增色不少。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5年初的一天上午,刚走到铁门前的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正拿着一把花剪,已将铁树所有的枝条拦腰剪截去了近三分之一,统统只剩下光秃秃的一段老枝,此时正好剪完最后一枝。顿时,我目瞪口呆,许久无言,只是在心中跟自己说:“好啦,今后再不用侍弄了,噢,枉费心机而已,谁叫你自作多情?将家中一盆极美的铁树搬到这里而遭此酷刑!……一个舒心优美的环境要靠大家来营造,算了,不想了”,我打断自己的思维,只觉得一颗心在隐隐作痛……此后,铁树便成了垃圾桶,痰盂缽,本已抽出的嫩芽很快便被几寸厚的废茶叶渣子所覆盖笼罩而难以见到天日,余下的光秃秃的枝丫也不再生长并逐渐现出黄叶……看着这个惨相,我的心情也随铁树一同慢慢枯萎。
二轮县志启动回眸及分工运作概况
2003年7月3日召开调整后的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
2003年8月7日。宿松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第15号《会议纪要》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纪要》决定:
(1)聘请朱加立、廖理南为《宿松县志》(1978-2002)副主编,并增补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
(2)聘请沈巧枝、吴自力为《宿松县志》(1978-2002)编辑。
2003年8月8日召开宿松县二轮修志工作会议;8月28日为期两天的全县二轮修志业务培训会在县供销社会议室举行;9月10日,又于林业大酒店会议室举办未参加首期培训的修志人员业务培训班。
自2003年9月14日始,已经到位的修志人员分工分口联系承编单位,上门指导业务,催征《安庆市志》所需的四项资料,了解修志的启动情况和进展动态,对征集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同时出台《安庆市志》宿松县资料工作初步分工。
2004年5月24日印发编修二轮县志各章(项)文字篇幅初步安排(讨论稿)。
2004年7月3日印发续修二轮县志编纂工作分工一览表。
2004年11月29日松编字[2004]03号《宿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会议纪要》……就有关事项决定如下:(1)略;(2)编修人员按两级聘任原则,同意朱家立同志辞去二轮县志副主编。续聘石兵同志为二轮县志副主编,由县政府颁发聘书;增聘朱亚夫、钟正德为编辑,连同原聘编辑,由编纂委员会颁发聘书……。
2005年5月16日印发续修二轮县志后期工程实施进度安排表(预案)。
廖道安的“主编权威”足以改变县政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部署
(1)上述第二部分已明确地知晓县政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聘请编辑的决定,而且颁发聘书写得清楚明白,是《宿松县志》(1978-2002)的编辑,而不是哪一阶段的编辑。
(2)2005年5月26日,陈森然副县长率县政府刘科长,财务局张科长至县志办公室开调研会,在陈副县长发言的第8条明确答复:“……关于沈编提到的县志办公室因经费紧缺而欲提前请外聘人员离开问题,没有此话,至少要等到县志出版再请大家……”。
(3)2005年9月30日在县志办结束分纂的会议上,廖道安振振有词地说:“……国庆节后制订总纂方案,向编委会主任汇报,等召开的编 纂委员会拍板定案后,再按其要求实施总纂,没有接到通知的编辑人员将不再安排总纂工作……”就在这次会议上,县志副主编针对廖的这一意见曾仗义执言地指出“这样做不妥,这些编辑,是县政府聘请来参与本届志书编写的,志书没有完稿合拢,他们不能中途离开”。实际上,国庆长假期间,县编纂委员会根本未召开会议,倒是县志办公室在廖道安一手操纵下于2005年10月9日召开会议并决定参加总纂人选,而擅自解聘了朱亚夫、钟正德和我。由此可以看出,廖道安权力无限,欺上瞒下,既是县志主编,又是县志办主任,亦能强奸县委、县政府、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及全体人员的意愿。
自2003年8月26日始,我在县志办公室的主要工作业绩
(1)据2003年11月19日统计,共催征到位四项资料及二轮县志资料共50余万字,报送单位:县联社、财险、人险,人行、建行、农行、农发行、中行、工行、粮食局、工商局、国税局、地税局、财政局、水产局、商务局、气象局、供销社、石油公司、农业委、林业局、水利局。
(2)至2005年12月底止,完成农林水财金(报送《安庆市志》资料)计4.3万字,完成二轮县志编纂;第七章综合经济管理(含计划、物价、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审计、统计、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第二十章财政、第二十一章税务、第二十二章金融,第二十三章保险、第四十四章民玫、第四十六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其中:(A)财政章共打印三稿,其余章均打印二稿。(B)2005年9月30日交手稿:农林水财金87页4.3万字;金融78页3.9万字;民政58页2.9万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0页1.5万字;财政133页6.65万字;税务35页1.75万字;保险17页0.9万字;综合经济管理130页,6.5万字。
廖道安排挤、打击我的言语、行为举例
(1)2004年5月,县志办在廖道安的组织下,开展了对试写三章的初稿进行评议。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是重点打击我,给其来个下马威。在廖一再的引导下,炮火终于集中到我试编的《财政》章上。不久,廖终于露出了本意,以行家的眼光和主编的资历评价我的初稿:篇幅过长,不应有名词解释,无图表(此前,我一再解释,因是试写,为节省复印费,只列了图表标题,如果主编觉得需哪份图表,再复印),而在以后的二、三稿修改过程中,缺一个名词解释都会令其补上!真的是让人无所适从。
(2)2004年7月3日编纂工作分工一览表上标注沈巧枝栏内有《艺文精选》,但在2005年6月的一次业务会上,廖未经开会研究即说:“《艺文精选》的编纂暂不进行,待后再定”。至2006年《艺文精选》编撰易人。
(3)2005年10月12日,廖在业务会上说:“沈编7章志稿初稿全部完成,只有保险1章写了第二稿,有5章未按主编提出的意见去修改……都是不合格的”。
(4)2006年元月4日上午,廖办公室内3人,先是黄某小声跟他讲修志补助的事,然后就听廖大声说:“这不行!是什么话?我们总纂忙得要死,发的钱比别人少,有的人不干事,还发得多(按照规定,退休人员每月修志补助费500元,未退休的为350元,)有的人的稿子要重写(补充修改是重写吗?那大家都一样)。不行!我要去找县长,找有些老同志。”
(5)2006年3月16日,廖在县志办公室会议上说:“沈是写小说的,不适合修志工作,我不会安排她参加总纂的,(权力大得可以吧?!)”。
(6)2006年5月18日,县政府分管陈县长与朱科长在县志办公室进行调研,谈到沈巧枝请假的问题,廖道安说:“沈巧枝能力不行,水平太差”。
试析廖道安排挤、打击我的心态由来
(1)关于《孚玉镇志》顾问的设置
1986年4月我自县酒厂借调进入县志办公室,参加第一轮《宿松县志》的编纂工作,5月正式调入,1989年初第一轮《宿松县志》稿送出版社后,我即于当年5月调离,进入县审计局工作,期间,《城关镇志》由我主编成稿,接着城关镇将之付梓成书,得到社会各界认同,第二轮《宿松县志》的编纂启动后,孚玉镇政府有意仍聘我主编《孚玉镇志》,并请示了分管县长,因我当时已知2003年8月7日《会议纪要》上已确定的聘请参加编纂二轮县志人员有自己的名字,乃专程请示新上任的县志办公室黄奏天主任。问询可否兼顾,黄表示不同意,言下之意是以免影响县志的工作,于是《孚玉镇志》改由熊武松同志主编,2005年初,廖道安向孚玉镇有关同志提出担任《孚玉镇志》顾问。不知何因,孚玉镇一直未发出关于设置顾问的信息,因而廖便怀恨在心,以为是我从中作梗。
(2)关于《宿松县志》“社会生活”中民俗资料的提供问题
2004年6月的一天,县志办主任黄奏天同志找我谈心:“沈编,听说你手头有些民俗资料,能否拿出来供县志使用?”我当时一楞,随即答道:“这要看分工的情况,如果社会生活分到我名下,我当然要拿出来,但如果不分到我名下,就有些不好说了……最后难以断定是谁的成果”。2004年7月3日编纂工作分工表出来后,“社会生活”分到了吴自力同志名下,因而当县志办有关领导及某项业务会上又提到这桩事时,我仍是上面的原话,未将几十年来所收集的民俗资料拱手送给廖主编,而是无报酬地提供给了《孚玉镇志》。
(3)妒嫉心的作祟
其一、早在2003年9月初,我很尊敬、很诚恳地对廖说:“廖主编,编纂工作开始后,对我的稿子一定要从工作出发,不留情面,并请不吝赐教……”哪知他皮笑肉不笑地回答我:“我哪敢修改你的稿子?!”我很诧异,小心探问:“您为什么会这样说?!”
廖也坦陈:“因为你参加过第一轮修志,又出版了两本小说集……”
“哦”,我当即回答:“第一轮修志已事隔多年,之后从事了十几年的审计工作,如今一切都得从头越……至于写小说,那是个人爱好,小说体与志体是两码事……”
其二,2004年,县诗词楹联协会吸收我入会,经陈正友老指点,我填好表后交给廖,请他转交。他接过表,不冷不热地问:“你从哪里搞来的表?!”我照直作答:“诗词楹联协会发的呀”。
(4)对于不识事体的我的憎恶
2004年元月15日县志办年度工作结束会上,廖先说了些客气话,接着话锋一转,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正月我不喜欢串门,也请各位不要到我家来串门……祝大家春节好。”“老天真”的我也就真的未去“串门”因而犯了“不敬”之忌,事隔两年,回味起来,才知廖的一番话语应翻译为当今流行的广告:“今年过节不收礼(呀),收礼还收脑白金”!!!
试披露些许廖道安的阴谋诡计
(1)据知情人士透露。廖道安不惜将其亡父抬出来,主动请缨,担任二轮县志主编的目的,一是想留名于史,二是想将大女儿调进县志办公室。
(2)抢权,越位
《地方志续修指南》P30:“主编在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领导下,负责志书业务编纂工作”,而廖却一再片面强调主编负责制。独揽县志办所有大小权力,稍不如意,便以“罢编不干”的故伎来要挟县志办及县政府领导;自己同是县志办的临时工,却反客为主,今天不要这个干,明天不要那个干,而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目的有二,一是排除异已,树立主编权威,为施展下一步阴谋铺平道路;二是节缩修志补助经费,转为其女儿的工资费用。
(3)利用主持业务会议的权利,煽动众编辑说服县志办黄主任在其女儿的合同上签字。
2004年初的一次业务会上,我们尊敬的廖道安主编很动情地说:“……其实大家都没有私心,还就只我有个私心,我的女儿调到县志办来的事到现在还无着落。我想先订个合同,可黄主任不签字”。
是呀,舔犊之情人皆有之,于是古道热肠的老编辑们纷纷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黄主任,你就签个字吧,免得廖主编心事重重,影响修志工作……黄主任当场无言,不久,黄果然就范,无奈地签了合同。
(4)利用骗取来的主编职务之便,经常与县志办公室领导和县政府领导讨价还价,稍不如意,就假口不干,目的还是为了女儿的调动,最明显的一次是,宿松县志办应于2003年12月底前上交市志办的宿松篇目的内容。2003年8月第二轮修志工作启动后,至2003年12月,各单位的四项资料基本按期交来,县志办各编辑亦按自个接受任务按时交稿,而廖却将资料一直压在自己抽屉里,整整两年后在市志办一再催促下才极不情愿地拿了出来。
(5)2006年元月5日,县志办公室发给县人事局的请核工资报告大意是:申请核批聘请(哪一级聘请的,聘书呐?!)人员廖秋平每月工资额计1072元;请看县志办发放修志补助经费的工资表上是“廖琼贻”!是两人还是同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两个名字?!
(6)为了使“唐僧肉”(县政府拨给的修志补助经费)最大限度地“肥水不流外人田”,经过又一次以“罢编”相逼相挟,2005年“五一”节后廖的女儿忽然来到县志办公室上班了,专职打印(其时,县志分纂初稿已基本完稿)先是要求每月工资按1072元发放,因县人事局未予核编,县志办公室感到为难,后采用了县计生委一位老资格的临时工的工资标准每月800元发放,廖先是不同意,接着又灵机一动,要求发给其女儿每月修志补助经费350元,好!县志办公室每月又凭空多出1150元的工资支出,人事局不核编,则财政局不予增拨。怎么办?!怎么办?!经过密谋,决定自2005年7月辞去3个人,这样每月便可腾出1200元,从而便解决了廖之女儿的工资。请看2006年元月11日县志办公室报出的财务报表;年末人数13人,其中:在职3人、退休2人,其他8人,2005年7月已辞1人,2005年10月先打算辞2人。结果因各种原因,只辞掉1人。所以,其他人数应为6人。按统计口径,上年年末人数为本年年初人数,那么,财政局核批修志补助经费即依据该报表人数,这不是明日张胆地虚报人员数目,骗取财政补贴么?!
(7)滥用主编淫威,施行“拉、打”术
2005年9月20日,廖喊石兵副主编至其办公室、小声说着什么,石开始不同意,并说:“各人写的稿子还是各人改,这样利于工作……”只听廖正色道:“你是副主编,应该支持我的工作。这是一个策略,就象林场折迁一样……”于是在2005年9月30日的分纂结束会议上,廖抛出了他的阴谋,并泡制了一份二轮县志分纂稿封面,并加上“二审后第×次修改本”的字样,另宣读了从前未曾提出过的要求和条件,作为针对某些人的借口。
(8)有步骤地打击、排挤他人,“顺眼者留,不合意者走”。
凡县志办公室及相关知情人士都清楚,小小一个宿松县地方志办公室自2003年8月26日启动运行,从2004年初至现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先后有朱家立同志的愤然辞职;廖理南同志由当初的仗义执言变为如今的懒得讲话(因讲了也只是白讲);朱亚夫同志的寻求解脱;钟正德的苦涩一笑,直至我的“落荒而逃”,不能不佩服廖大主编欺上瞒下,阴险狡诈、玩弄权术伎俩之“炉火纯青”啊!
(9)按照原计划,二轮县志应于2005年12月底交付出版社,可在廖的掌控下,计划时间一再后延,众所周知,廖道安在2005年三季度曾向当时的县长章松同志拍胸保证:誓在2006年春节前将总纂初稿拿出来!不然,则“引咎辞职”!结果怎么样?!只是又一次巧舌如簧的忽悠而已,于是又顺延至2006年6月,2006年8月……直至不能再拖而止,目的只有一个,尽可能地多搞些修志补助费,过了这个村就无此店哪(59岁现象的又一精彩体现)!
 我与廖道安在业务上的分岐略叙
(一)关于篇目的设置(由于篇幅所限,只举数例)
关于二轮县志的篇目,廖道安主编可谓“呕心沥血”,先是比照省内外各市县志篇目,又参考上一轮县志篇目,也征求过各方意见,先后数次易稿,至2004年8月2日,仍存在多处值得商榷之处:
(1)第五章为经济体制改革,第六章为政治体制改革,但在各专章中,基本都设立了“管理体制”的节目;第37章《劳动与社会保障》中的第六节设“社会保障”,第44章《民政》第五节设“社会保障”……以至于2005年10月总纂开始时,3人专门集中1个月的时间处理交叉重复问题,至于处理得怎样,尚不得而知。
(2)第二十三章《保险》的内容不多,可纳于《金融》章中,而且缺少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的内容,使若干年后以2003年为上限的第三轮《宿松县志》缺失了上述两个保险的起步资料。
(3)县志是有一定容量的,但必须有个限度,如果篇目设立过细,则会导致内容拉杂,混同于一般部门志和专业志,如:《金融》章中第九节“安全保卫”、第十节“队伍建设”当属删减内容,其它章中也有类似情况:
(4)图表过多、过细,如《金融》章中的《1978年以来县内流通货币及债券,证券票样照片》,流通货币是全国统一的债券,证券票样亦如此,真要记载,只需记载县内企业发行的企业债券即可。
(5)有些行业有其一定的营销模式及营销策略,亦是商业秘密,如第二十三章《保险》中第二节《险种》中的市场营销目则很难写,因为,某些营销举措,企业是不会轻易示人的。
(二)出于对工作的热情,对修志工作的热爱,对二轮县志负责,我曾大胆率直地提出了不少建议,可能伤及了主编的自尊与自主:
(1)如《财政》章中“定额上交(补贴)、递增(减)”中的括号及其内容不能省略,而廖在审稿时划去了,我在修改时据理力争,未按主编的意愿进行删减。
(2)从志稿的科学性出发及考虑宿松地理位置特殊性,我建议并力争增加了“农村社会经济调查”一切(廖开始不同意,后来虽然勉强同意了,但却怀恨在心)。
(3)增补了“审计”中“国家审计”及其具体内容,建议删去了“案件审计”的目次。
(4)《金融》章中建议增写了“住房公积金存贷款、邮政储蓄”等内容。
说几句疯话
二轮县志的“十月怀胎”即呈“先天不足之状”,依据如下:
首先,且不说其他市县多是志办主任与主编一肩挑,只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2003年7月到任的黄奏天主任是新提拔的副科级,而给其配任的县志主编廖道安则是较其资格相对较老的正科级,来之前虽然已去掉了政协办公室主任的大权,但自认为是梆梆硬的正科级。中国有句俗话叫“官大一级压死牛”,虽然只差半级,但也足以压制或控制住一个刚刚提拔的老实巴交的黄奏天主任,在此轮修志中,虽说只是业务上是主编负责制,但如将业务范围扩至无穷大呐?再逞强霸道一点,偶尔玩个心眼,耍下花枪,稍不如意便以“罢编”相挟呢?……所以,县志办公室的同志都听到过这样的喟叹:“有什么办法?副科能领导正科么?!”。
其次,自启动二轮县志编写工作以来,县志办公室的关键人物是黄奏天主任,廖道安主编(聘请),廖理南副主编,这三位凑巧都是北浴乡人,且以前同在一所山村学校任教。“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用在这里是再合适不过了,且2005年5月又增加了廖道安的女儿,于是小小的县志办公室真的成为三廖一黄的“一家村、两姓店”。
三,二轮县志》启动之初,即2003年8月29日的全县修志人员业务培训会上,作为主编的廖道安同志首先要求并一再强调各承编单位,在2003年9-10月完成1978-2002年的“情况综述、大事简介,人物资料、图片资料”等四项资料,致使相当一部分修志人员及相关领导误以为此次会议只要求完成四项资料就行了,以致有些单位在完成了四项资料的搜集整理后便解散了修志班子,故使后来征集县志所需资料遇到了很多难题。
四,二轮县志》的篇目虽六易其稿,但仍缺乏科学性,简洁性、过细过杂、交叉重复太多,与其在总纂时集中大量时间和人力进行处理,就不如在修订篇目时即时删减,以免浪费掉大量的时间、人力、笔墨、纸张。篇目是纲,“纲举目张”,如果“纲”举不起,则“其目难张”。
五,二轮县志》启动以来,修志业务主管不遵循预先制订的管理办法、人员分工等程序操作,随意性严重,致修志工作蹒跚难行,如2003年9月1 4日《安庆市志》宿松县资料工作初步分工中各编辑栏下的第5条“参与上报市志办,资料稿件的互审、评议、修改”,关于上报市志办的资料,编辑们都未见到过,更不谈“互审、评议、修改”了,当然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报上去的,至于未按照县志办制定的其他分工、安排、进度等一系列措施去运作就不一一列举。
六,我们水平极高的廖道安平时一再在县志办领导面前进言,并屡次在业务会上,直至2006年5月18日还在陈副县长和两位科长至县志办调研的会议上斩钉截铁地重申:“沈巧枝能力不行,水平太差,编县志力不从心。”
是的,我已老了,有些事确是力不从心、所幸还未老昏头,没有主动请缨担当县志主编,也有同志推荐我当副主编,我仍然不敢贸然接受,只是摇首微笑婉拒。在此,无妨摘录《地方志续修指南》中《方志的文体文风》P57:“方志的语言”中一段话(2003年8月1 8日县志办公室第一期《宿松志讯》P14亦摘录):……语言是交流思想和信息的媒介……可以这么说,正确地使用语言,是编纂地方志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编纂者必备的基本功,地方志工作者,有了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修志就可以得心应手……。
从以下事实足可证明我能够正确地使用语言:
(1)1986-1989年,我参与了建国首轮《宿松县志》编纂,承编的是:卷九 工业,卷十 交通,卷十一 邮电,卷十二 城乡建设,卷十五 财税、金融,卷二十六 附录的第七章 新编《宿松县志》编纂始末。
(2)20世纪90年代初,独立完成了《城关镇志》的主编工作,后由孚玉镇出版成书。
(3)2003年8月7日被县政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聘请为《宿松县志》(1978-2002)编辑。
(4)自20世纪80年代即在《安徽文学》、《满江红》、《安庆报》、《安庆日报》及宿松县的文学报刊上发表了数量不少的文学作品,并于21世纪初连续出版了两本小说集。
(5)中国及世界著名的女作家石楠同志欣然应邀为我的第一个小说集作序。
或许,以上所述也能说明一点:上述有关决策的领导,建议者、相关的主编、编辑和大作家皆缺乏如廖道安主编的过人洞察力和鉴赏力,一错再错地将其文章发表,一错再错地聘其为《宿松县志》编辑,一错再错地为其主编出版小说集,却识不破沈其实“水平太差”!
试作一点预言
根据已披露及尚未列举的诸多复杂因素,我们可以想见得到这样一个现实:自2003年6月份以来,虽然宿松县委、县政府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人力、物力,但二轮县志》付梓后肯定会存在诸多难以规避的硬伤,即是说很可能将会是一副“残疾之躯”。肯定,这个结局是任何人都不愿见到的!然而,某些已经注定并形成了的事实是不会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过,我相信,宿松县委、县政府及宿松的广大人民还是不会嫌弃的,就如某些不幸的父母虽然生下的孩子有智障或肢体残疾,也定会对其疼爱有加并百般呵护,竭尽全力为其诊治,寻求改善或康复之良方妙药,虽然极其麻烦和辛苦,但那是却之不得的义务和责任。奈何!奈何!
尾声
我曾于2004年《宿松吟苑》发表过一首答友人的诗,现摘抄前睽如下:
潜心撰志不言愁  笔墨书笺共作俦
细剪精修勤奋撷  丹心赤胆谱春秋
人生长短凭天定  航道迂回任我游
最慰文坛交挚友  羊城宿邑共吟呕
今又步其原韵作诗一首,用以结束本文:
全力撰志无他求  不料主编暗相仇
如剑利语时嘲讥  度日如年写春秋
三十六计走为上  海阔天高任遨游
最慰文坛多挚友  相携互励共吟呕
二OO六年六月十九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