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春夏之交,田里的新粮还没泛黄,家里的陈粮早就吃完了,米缸空得像洗过的锅。 这时候,全家唯一的指望,就是公社发的那张粮食供应证。拿着这证,就能去粮站籴米。我家人口多,按规定能买四百斤。可每百斤米要十四块钱,四百斤就是五十六块,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家里根本拿不出这笔钱。队里有门路的,都去信用社贷款,先把这救命的粮食买回来再说。而我家没有门路,只能把供应证上的指标卖掉一半,用换来的钱买另一半米。这都是剜肉补疮的无奈法子。 那段时间,父亲总爱蹲在灶台前抽黄烟,一言不发,闷着头,眉头拧成个疙瘩。他愁的,就是这几十块的买米钱。家里没别的挣钱路子,父母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来,脸朝黄土背朝天,挣的工分还不够一家人糊口。我下面还有三个弟妹,年纪都小,都在上学。全家能出去挣点现钱的,就只有我这个半大的孩子,靠的是背着一面鼓,走村串队去说大鼓书。 那时候,听评书是村里人最大的乐趣。张贺芳的《呼杨合兵》、刘兰芳的《杨家将》、单田芳的《明英烈》等,一到中午十二点,哪怕地里的活再忙,也得撂下农具,守着收音机听。我家没有收音机,就跑到邻居家挤着听。评书是好听,可毕竟是北方的调调,我们南方人听着,总觉得不如大鼓书那样悦耳,连说带唱,鼓板伴奏,点缀情节,抑扬顿挫, 舒情达意。 我一点一点地攒了五毛钱,揣在兜里,走了十八里路,到区上的邮局,把钱汇给了花山文艺出版社。过了些日子,寄来了盼望已久的《明英烈》第一册《武科场》,单田芳的本子,油墨的香气直入鼻孔。 一翻开书,我就放不下了,字里行间的情节像钩子一样把我勾住。我废寝忘食地读,把书里的情节、正反面人物的名字和长相、各人使的兵器,都在心里默记下来,还琢磨着哪些情节适合唱得荡气回肠、哪些段落适合用大白话讲才惊心动魄,等全记熟了,就背上鼓,去了邻县大山里的村庄。 邻村的乡亲们爱听书,人也实在。书场就设在队屋里,地上西边靠墙,堆着一大堆最近砍伐的杉树,大伙就坐在树上,孩子们则站在周围看我说演《明英烈》。都听过单老的评书,可是,用我们宿松大鼓书说唱这书,乡亲们倍感新鲜和亲切。书场上,欢笑声不断,弥漫着山里人朴素的喝彩声,当说到常遇春马踏武科场,一泡马尿,救了全场英雄时,瞬间全场沸腾了。大婶婶们笑得直呼哎哟;放牛娃子们笑着说,怎么不是牛尿啊?老人们赶紧喝住别吵!可惜那本书太短,连说四场就说完了。社员们要求接着说,我只好无奈地实话相告:后面的没有书,说不来!大家满脸失望,静了片刻,队长跟我说:“队里没现钱给你,队屋里堆着的杉木,你随便扛一根走,就当你的说书钱。” 我连忙说:“叔,这杉木金贵,不止我四场书的价啊……”旁边的社员们都笑了:“傻小子,别算那么细!捡根大的扛,多出的就当送你了。你这点小个子,就算扛根最大的,也多不了多少。”我一股少年意气混着些许贪婪,就说:“好!那多谢叔伯们了!”我在那堆杉木里挑了一根又粗又直、皮色光亮的好杉木,弯下腰,双手捧住蔸部,用力往上抱,一猫腰,放上右肩,停了一停,肩膀贴着杉木往后退,直到树梢离开地面,整根的重量全部压在我肩上,才算扛起来了,直压得我肩膀生疼,腿有点颤,骨头逢里都咯吱吱响。我咬紧牙,心里在提醒自己,这可是四百斤救命米的唯一希望啊! 杉木硬是被我扛出了队屋的大门!队长看了有点惊讶,赶忙拿过一根杵杈,我接过杵杈立在胸前叉住杉木,抽出肩膀长长地松了口气,扭回头冲队长和社员叔叔们微笑答谢。队长笑着打趣:“路上多歇歇,压弯了腰,结不得‘马马’(老婆),莫怪我!”后面又是一阵哄笑。 回家的山路,足有二十里,窄窄的山路,曲曲弯弯,高高低低,上坡路占了一半多,在杵杈的助力下,我也只走了一段,就觉得杉木像钉子一样钉在我肩上,硬要把人钉进土里似的,越来越沉,胸腔里火烧火燎,臭汗和着灰尘钻进眼里,一片模糊,鞋子里进了沙石子,硌着脚底,疼得要命,眼前山路在摇晃,前路漫漫,望不到头。 这树少说也有一百五六十斤,看来今天是要压碎我这副少年骨架了,绝望像虫子一样爬上心头。正在这时,后面来了个小伙子,是他们村上的,他二话不说,弯腰托起树的另一头,说:“来,我帮你抬!”这位兄弟恰好在我县学竹篾匠,今天正好去师父家,与我可以同一段路。原本这么重的活,除了自家人,是不应该劳烦别人的,何况非亲非故,素不相识。此刻,我正像一个身陷绝境的落井者,突然有人伸出救援之手,是身不由已,不容拒绝的,连句虚假的客套话都没说,就欣然接受了这份善意。 我俩一人扛一头,深一脚浅一脚,翻山越岭,负重前行,他一直帮我扛到离家不远的路口,才转道去他师傅家。望着他的背影,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仅仅听过我说的几场书,就甘愿付出这么多汗水,甚至都没来得急问他姓名,是真的这么巧吗?突然想起队长和社员们目送我扛着杉木出村的情景,个个眼神里除了不舍,还有怜爱啊!想必是他父母有意安排的吧,一阵热血由心里直上头顶,眼泪莫名地落下。 父亲从地里回来,慢慢伸出长满老茧的手,摸着这根杉木,转脸看着我:是你一个人扛回来的?我说,有个兄弟帮我抬了一段路。父亲背过脸,母亲轻轻拉开我的衣领,扭头一看,呀,肩头又红又肿,都破皮了,淡淡的血水粘着树皮屑和着汗水浸湿了衣领,母亲已泪流满面。 第二天,父亲把这根含着我的汗水和陌生大哥温度的杉木扛去集镇上卖了,买回来了供应米。米粒倒进米缸,形成一片美丽的瀑布,带着悦耳的旋律填满了空荡荡的米缸,笼罩在家里许久的愁云,顷刻间被这瀑布冲得无影无踪。 那鼓声,那汗水,那杉木,那陌生人的肩膀,终于化作米缸里沉甸甸的安稳和踏实。 书声换来的,不仅仅是米饭香,更有一家人生活下去的底气。
作者简介 贺笃洪,男,1965年3月生,汉族,安徽宿松人,现住趾凤乡吴河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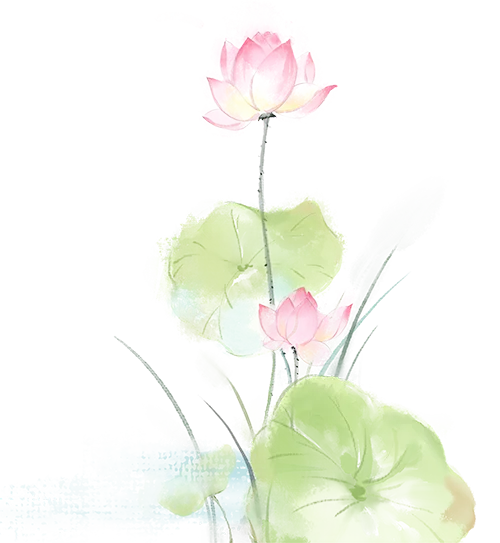
来源:宿松县文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