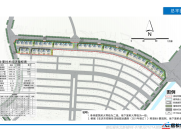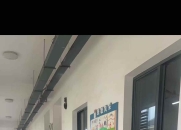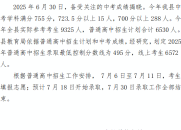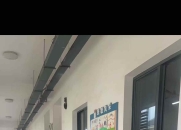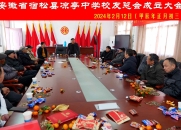|
|
早晨在公交站台等车时,遇到一个女同。很明显的女同特征,而且是位1(同性恋中扮演女角的那一方叫0,男角为1)。个子不高,最多1米55,穿松糕底儿一样厚的运动鞋,牛仔裤上有暗褐的铆钉,白色棉布短袖,胸襟处画着一个撅起的大红唇,后背是一排红字“Miss You”,涂了极浓的眼线膏,头发打过“摩丝”,一大溜儿一大溜儿向后蓬张着。整体形象酷似泰剧《Yes or No》里的那位“男”角。上班高峰期的马路堵得像打翻了一碗浆糊,从十字路口向几条主干线缓缓流动开去,黏稠而沉闷。公交车至少25分钟了还不来,身边开始有人骂骂咧咧。我盯着她,小心翼翼、不言不语,并且假装焦急不停绕圈踱步,从各个侧面观察她。我承认,这是一种很不礼貌且下作的行为,但你不能否认人类猎奇心的强大威力。
也许是觉察到了我的凝视,她看似无意地转头,奇怪地瞟了我一眼,仿佛要说什么,又撇撇嘴,迅速低头,扭身绕在了一个格子衬衫的男人身后。我猝不及防,只能尴尬地移开视线,一会儿仰头看天,一会低眼盯鞋,拙劣地扮演着路人甲。幸好车子及时赶到,救了某个无耻的偷窥者一命。
路上一直在想那个女孩的眼神,那种有点生气且无奈却欲言又止的感觉很是似曾相识。我念小学时周末趁大人外出,常常拿自己家座机给暗恋的男生打电话,某日放学路上捡到“神秘电话会所”的传单一张,从此开始拨打6XXXXXXX语音台,偷偷听“两性私语”、“情感夜话”云云(咳咳,这不叫早熟,叫早慧),连续几个月家中话费高达两百大洋之巨。九十年代的普通工薪家庭,每月供两百元话费还是有点吃力的。我爸问我:“你是不是用咱家电话打长途了?”我当然一边装模作样写作业一边矢口否认。大人疑惑之余只能迁怒于电信部门的丧尽天良。终于在1998年的某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时电视上天天在抗洪救灾,我妈一位在电信局上班的熟人,帮忙打印了一张长长的话费单子,一切小动作东窗事发,一顿饱揍。我妈一边打一边问:“这个电话号(暗恋男孩家的号码)谁家的?”我倒是长了骨气,蜷在墙角宁死不屈。我妈当时是指着我鼻子说:“你别能(注:能,陕北方言,得瑟的意思),迟早我查出来,小小年纪描眉画眼谈情说爱!”大约后来她也觉得丢人,此事不了了之。
十四年过去了,看到那女同姑娘的眼神时,突然想起这件事。我当年挨打时,也是这么看着我妈吧?那种惶恐害怕、似乎有难言之隐的眼神,明亮、尖锐、敏感、躲闪、不安又不愿屈服。光线变幻的瞳孔后是不是掩藏了她复杂的心情?或许她是想告诉我什么,又无力去为自己辩解呢?
我今天本不该如此盯她。没错,她是个女同,我也在天天口头声援着支持同性恋,却潜意识里把她当作怪物一样研究,甚至到了单位还绘声绘色描述给同事,像个长舌且八卦的市井大妈。而她有什么错呢?香港艺人黄耀明前几天面对媒体高调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次日发微博说“谁介意晚节会不保,笑一笑已苍老”,是啊,为何要给“爱”缚起无数恼人的茧丝呢?爱本身就是世上最美好、最无辜、最清澈的东西啊。那受伤小兽自舔伤口般的目光,让人心碎。如果时间能回到几个小时前,我想我会走过去抱抱她,告诉她:上帝作证,你是一个好姑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