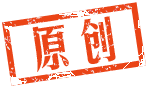|
|
司命树(1)
石普水
我们屋场不大,中间一条大路,东边住着石、徐二姓,西边住着尹、洪二姓。屋西边三棵大枫树,人称“把门将军”。屋东边是一片茂密的栗树峦。南边有一口小塘,塘东边一棵大朴树,西边一棵“司命树”——家乡方言重,叫它“司命树”,或者该写作“私苗树”“司明树”“丝棉树”,博学君子为我正之。司命树树枝笔直向上长,尖尖细叶也片片向上,形状象杨树叶但比杨树叶俊美。老人口口相传,这树有三百来岁,主一屋风水,动它一根枝一根杈就有地方要死人的。
两棵大树中间住着一户人家,三间破屋,总面积不过50平米。两间瓦屋,一间茅草屋。西边一间前面是主房。中间隔着一堵土砖墙,后边是猪、牛栏。中间一间是堂厅,地面坑洼不平。没有后门,也没窗户,两块亮瓦,晴天屋内都显得阴暗。瓦上很多树叶,被鸟雀弄得乱七八糟的破瓦,下雨时外边大落家内小落,到处摆满水桶脸盆等接屋露的家什。墙后正中贴着一张毛主席像,向右倾斜至少15度角,左角垂下,盖住了领袖半边脸。东边是一间小茅草屋,一扇窗户两本书大小,竖着三根弯曲的直档。茅屋里靠近窗户是土砖灶,灶上一口锅,两口汤罐,前边煮猪食,后边烧热水。石灰拌黄泥的灶面没有很抹平,且破损不少,稍用力一洗便会洗出泥巴水。平头灶,没有烟囱,烧柴时火苗带烟冲出灶门,把灶前煮猪食的汤罐一方烧得漆黑漆黑。茅草屋上吊着一根又一根黑黑的烟尘,随风飘荡,一道独特的景观。灶东边有一口小水缸,两只旧木水桶,大的在缸边,小的挂在屋上的木桶钩上。西边一个破柜是放碗筷的。屋很矮,高个子进屋不能抬头。我伸手也能拉下屋顶上的茅草。屋后架着一张破竹床,靠近它便吱吱叽叽地响,发出垂老的呻吟。竹床上一把破絮,可能是清朝的文物,黑絮筋牵扯着,大大小小百十来个洞。破被子歪歪扭扭地躺在床上有点像军用地图。分不清什么颜色,跟烟熏火燎的土墙浑然一体,很是般配。
我把睡竹床上的主人叫二舅。其实不是亲娘舅,跟我母亲同一辈份。大舅名叫“花子”,小时候他是名副其实的讨饭的“叫花子”。二舅排行老二,按本地约定俗成的规矩人们都把他叫“二花”。修谱时坐谱堂的先生嫌不雅,引经据典,说“华、花”同源,给他取名叫“二华”,一个挺时髦的名字。
但是人们叫“二华”谱名的不多。有道是“有钱王八三个号”,二舅没有钱,但不只三个号。他家老三逃荒到新疆,托一位半通不通的先生写来一封信,信中称父母为“二老”。二舅在旁边听着,好生懊恼,自言自语:“这个‘三癞痢’,一声哥哥都不叫!”。——他不知道二老是称呼父母,认为这癞痢头老三把他这位二哥叫“二老(佬)”。好事者传为笑柄,都打趣他叫“二佬”。
叫他“老八点”也是有典故的。三年自然灾害时,二舅跑到华阳河农场,几年后衣锦还乡,穿着四个口袋的中山装,戴着三块瓦的帽子,远看衣帽近看人,远看二舅新衣新帽像个国家干部似的。特别手上那块手表,那可是万众瞩目,像“神舟七号”上翟志刚出现似的。二舅故意把袖子捋得老高老高,惹来无数羡慕的眼光。二舅不识字,中午,有人问他:“二佬,几点钟?”他煞有介事地看看说:“八点吧!”后来人们又叫他“老八点”。
二舅耳朵有点聋,年纪大点的人都当面叫他“二聋子”。
二舅很喜欢我,他把手表给我戴,还讲故事给我听。
“四个聋子一块走路,第一个聋子放了个屁,第二个聋子说:‘讲么事呀?’第三个聋子说‘是倒也是!’第四个聋子说:‘瞎子看见鬼一大堆。’”
这是二舅故事的原文。二舅方言重,我给您翻译:四个聋子一块走路,第一个聋子放了个屁,第二个聋子没听出来是放屁,还以为是跟他说话,便问:“讲什么呀?”第三个聋子也没听清是放屁,不肯承认自己耳聋,便也含糊其辞地附和着说:“是这么一回事!”第四个聋子根本没听清前面几位放屁和说什么话,他别出心裁地说:“瞎子看见鬼一大堆。”
后来我明白,这是人们讽刺和打趣聋子的笑话。二舅却像阿q对小伙计似的向我炫耀。(2009.11.26.)(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