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禅宗文脉佛坐岭
夏业柱

我不懂禅,也不信禅,对禅宗毫无研究,偶尔听说,觉得玄。宿松采风,忽然走近佛坐岭,在五祖禅院旁的小木屋,正儿八经小住了一夜,依稀像做梦。我们头天到,第二天回,不到一昼夜,除了吃睡和玩牌,竟然上了两趟佛坐岭,还钻了一回石莲洞,把大小禅宗遗迹,囫囵吞枣地走马了一遍,边走边听宿松人介绍,我感觉像是在恶补禅文化。
在皖山皖水中,佛坐岭很小,小到出了宿松,便无人知晓,我此前从没听说过。然而在宿松人心中,它不寻常,倒不在风景,也不在美食,全在禅。“禅”字让佛坐岭形在尘世,意在世外。史传唐代僧人弘仁就因看中佛坐岭,特意由湖北来安徽,落脚宿松。那时宿松并不繁盛,佛坐岭更是穷乡僻壤,拥有的只有松石林泉、飞禽走兽,没想到偏偏合了佛家心意。弘仁于是立志建寺,弘法修行。弘仁乃禅宗五祖,道行深,声望高,弘法也特别。山腰有一巨石,状如靠椅,相传曾是他讲经处,当地人叫佛坐石,石由佛得名,山又由石得名。我看佛坐石,倚在秋枫下,有青苔覆盖的古意,但我不信能讲经,它凹凸不平,难以打坐,下方又狭小,几无立锥之地,此处讲经,岂不空对山石?不过禅宗“以心传心”,没准取的就是意会,而非言传。实在的证据似乎在禅院,建了毁,毁了建,赵朴初还题了名,想必是真货。我没能考证禅院的曲折由来,只约略打探到现状,如今是见忍主持,他也由湖北来此修行。禅宗史上,湖北是出了名的,四祖寺、五祖寺都在黄梅,千百年香火不断,见忍在那里当过20年主持,得了真传,后来也像弘仁,选中佛坐岭。我没见到见忍,听说在闭关。但我听说他是一个精于书画诗文和音乐的和尚,化缘8000万元,复建五祖禅院,佩服他很了得。
五祖禅院如今成了佛坐岭脸面,也是宿松作为禅宗佛地的资本。但宿松人不爱啃老本,他们脑子活、主意多。同是佛坐岭,还是禅文化,他们却打出了新品牌。把苍老的佛坐岭囊括进大景区,叫了时髦又响亮的名号——石莲洞国家森林公园。我乍听此说,脑子忽而转到花果山,忽而想成植物园,唯独没想到禅宗。这可能正是宿松人的聪明,有意给外来客惊喜。石莲洞卧在山腰,曲折幽长,旧时叫十里洞,因宿松口音“里”、“莲”不分,后改叫石莲洞。但我想或与洞顶有关,石莲洞是溶洞,洞顶钟乳石状如莲花,叫石莲洞未尝不好,而名字一改,意境要深远许多。何况弘仁在洞里面壁过,洞壁还有他的自咏诗,“吹吹白发下青山,七岁归来改旧颜,人却少年松却老,是非从此落人间”。而康熙时,干脆以石莲洞为授法洞,以洞顶石上青莲为峰顶池上白莲,石莲洞从此与佛国缘分更深。实际上千百年来,文人雅士来佛坐岭皆为石莲洞,或游历,或隐居,其禅宗文脉如禅院香火,从未间断。我在洞中,寻访到一尊古雕像,貌似玄奘,隐于阴暗处,为洞中奇景。但何人何时所立,立者何意,至今无解。我想无论来历如何,供在洞中,适得其所。而洞口“石莲洞”三字更有来历,据说是唐代文士罗隐真迹,罗隐名字即如其身世,他一生不得志,落寞时曾在石莲洞隐居。他的诗《赠宿松傅少府》、《皖泊宿松》,写的就是佛坐岭一带的隐居生活。罗隐不是宿松人,也没在宿松当过芝麻官,却情系宿松,这不能不归因于佛坐岭和石莲洞的魅力。
森林公园叫响时间不长,效果却明显,全因有岭、有洞、有禅院,接禅宗底气。我沿小路上山,秋风吹拂,层林尽染,一路遗迹散落林间,感觉在禅宗文脉中穿越。分经台,仙鹤石,五祖庭,龙啸石,听雨亭,对酌亭,都大有来头。因了仓促,我捡一丢三,唯罗隐、萧统、李白记得一二。萧统是梁太子,本该笙歌于金陵,没想他躲到这里,以石为台,翻译《金刚经》,也是有他,晦涩的经书才为寻常信徒接受,译经石从此叫了分经台。要说弘仁、罗隐、萧统也算是同道,都冲佛而来,李白则不同,他从九江来,只为与县令对酌,实在令人回味。李白乘舟的码头尚在佛坐岭下二郎河边,河岸的南台即是对饮处,与佛坐岭隔山相望,我从山上遥望,南台一片迷蒙的秋色,可惜我们未及光顾。且不管李白是云游还是交友,放荡不羁的他,游遍名山大川,能在小小佛坐岭歇脚多日,还激动地写了六首诗,不能不令人感慨,而佛坐岭因了李白,陡增文意,从此薪火相传,文脉不断。
我没读李白诗,不知道他心中是怎样的佛坐岭,也没看萧统的《金刚经》,不知道佛坐岭与佛有什么天然联系。但我相信佛坐岭是宝地,适合静心。我在禅院小转时,登高望远,秋山逶迤,远水无波,好一派钟灵毓秀之气。那时天气尚早,没有香客,和尚想必都在早课,禅院静悄悄、空荡荡,正应了禅宗的遁世意味。我只遇见两人,一僧一俗,僧男俗女,搭配得很巧合。俗人是黄梅来的义工,中年女居士,崇拜见忍,言语中透出虔诚,却不知因何没出家。僧人是小伙子,法号悟善,老家广西,曾专攻书画,上月才落发。但他住惕不在佛坐岭,是在陕西终南山,来此是为学习,明年回寺受戒。我对悟善身世好奇,想与他合影,而他看重佛缘,不愿合影,只加微信祝我“早成佛道”,我不知所言。告别悟善,我脑子里冒出了“天下禅宗”,小小佛坐岭偏居宿松,竟连着天下,这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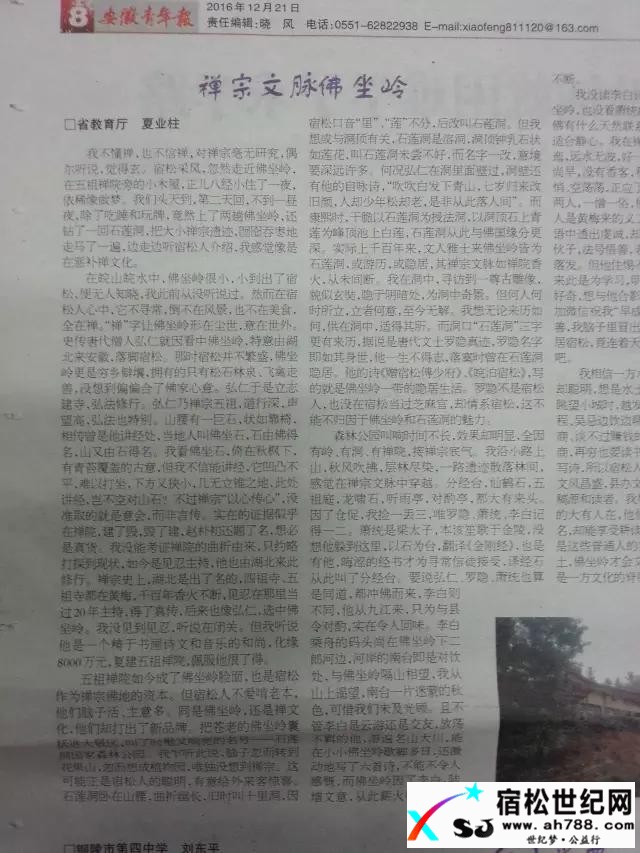
我相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宿松方言怪,人却聪明,想是水土养人。我站在禅院钟鼓楼前眺望小城时,越发感叹。晚餐时,宿松作家刘鹏程、吴忌边饮边聊,似乎给了答案。在言不过经商、谈不过赚钱的年代,宿松人很例外,重文轻商,再穷也要读书,而读书不为官、不为钱,却为写诗,所以宿松人口不多,土诗人一大把。也是文风昌盛,县办文学小刊堪比省城大报,从不缺稿源和读者。我后来上网搜,写佛坐岭、石莲洞的大有人在,他们都很普通,或许终身不曾扬名,却能享受耕读山林之乐,实在难得。我想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坚守,宿松大地才有了人文水土,佛坐岭才会文脉不断,禅宗永存吧,他们才是一方文化的脊梁。 ——转自《安徽青年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