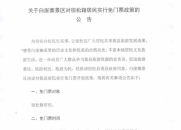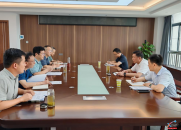|
283、回家(99) 石普水 老天终于降温了,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人也心平气和了。 民以食为天。雨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抓紧时间种菜。种菜分期分批,一场雨种一样菜,一样菜种一墒。最先种的是白菜,妻说苏州青最好吃,下包菜秧,第二场雨种的是120天的萝卜菜。同时已经挖好了一个墒子,等着下雨栽种大蒜,还要种芹菜、莴笋。妻是总指挥,有计划地安排。我们种菜分工明确,各尽其能。我挖土,妻平整掏沟;我浇水粪,妻撒种子;我撒火粪,妻掩种平墒。种菜一般在下午,劳动量不大,三下两下做完了。种菜更是一种乐趣。今天种菜,明天、后天就会有菜芽破土而出,看着嫩嫩的绿色,一份欣喜,一份惊奇,一份感动,一种希望,跟着接踵而来。 “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了你浇园” 。在年轻人逐渐减少的乡村,我不合时宜地留下来与土地对话,而且刀耕火种,重复着祖祖辈辈们男耕女织的生活,与世无争,颐养天年。人生之乐,追求“人到无求品自高”,欣赏“醉里吴音相媚好”。 天气变凉了,下午我去割柴。割柴本是老娘们的事,但是我从小喜欢割柴,到老这个习惯依然没有改变。秋风阵阵,艳阳高照,泡上一杯茶,换上不知何年何月的旧衣服,乔装打扮,喜滋滋地拿着一杯茶一个马儿出门。一把五块钱的新镰刀,长长的铁柄,镰刀上写着“日本钢”。我不大喜欢小日本,但是不得不承认日本科技实在发达。果然“人强不如物毒”,小日本的钢真的好,割起柴来一挥而就,毫不费力。转眼身后倒下一大片,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劳逸结合,割了一会,喝一口茶,坐在马儿上扭把儿,自我陶醉,兴致勃勃。傍晚时,妻也来扭把儿了,并且带来一些陈芝麻烂谷子新闻,饶有兴致地向我播报。我成了她热心听众。很早就学会了聆听,静静地听着,通常,她的新闻我会在博客上播报的,但是有一条新闻我却不愿播报—— 一个高中生不明不白的死了。他曾经是佐坝中学的学生。老师说他是一个聪明好学,文质彬彬的好学生。前年640分考上宿松二中,暑假住在县城的外公家,失踪两天,最后在河里找到。5天后火化,公安局说是自杀。为什么“自杀”?是不堪外部学习压力还是心理素质差?…… 我不想讨论这个比泰山还要沉重的话题…… 天气转凉后做了两件大事,两件大好事。 第一是把楼房旁边那间民房木楼上几千几百年前的陈柴一一搬到前面。这些灰灰的黄黄的陈柴已经有长长的历史了。芝麻杆,花生禾,甚至还有山上挖的“芭茅草” ,想来都历史悠久,可以评为文物等级了。楼房是1997年做的,这些陈柴想来都是上世纪的作品。但是,这些“芭茅草”来自何年何月,需要认真考证,我不敢妄下结论。现代中国人可能再没有人挖芭茅草了。那一钯一钯挖起来的芭茅草,很可能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尽管可能不再烧它们了,但是我不忍心扔掉,那是时代的见证啊! 第二是把院子里里外外的沟全部铲得光溜溜的,好像人剃头了一样,看上去顺眼多了。然后把乌黑乌黑的土巴铲起来,晒干。把清明伐树的碎树叶碎树枝,把花生叶,把屋前后树叶,全部放在土巴上面烧火粪,这是中国几千年流传的农家肥,种菜的绿色肥料。看到屋前屋后,树下都光溜溜的,这是一个勤劳的老农民的所作所为,我自我陶醉。 (2013.9.5.八月初一)(1266)(201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