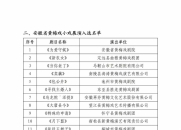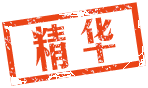|
【宿松乡贤】好汉坡上乡贤沈互和的故事(1) 石普水 高岭与太湖毗邻的地方有一道很长的坡,叫“好汉坡”。在人拉肩扛的年代靠花车运输,能够一口气推上这道坡的,自然是人人竖大拇指力大无穷的好汉。 好汉坡边的农民沈互和,个子不高,精廋,全然没有高大威猛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古铜色的脸上刻下岁月的深深沟壑,瘪嘴,说话慢吞吞的,不是伶牙俐齿能说会道的人物,这位,就是高岭乡党委书记介绍的乡贤,我和这位乡贤在高岭乡会议室里开始了对话。 您是党员吗?——不是。 您今年高寿?——68岁。满头灰白色的头发,一个上世纪60年代饱经沧桑的典型的贫下中农形象。 你们汪冲村沈家大屋今年在环境整治、拆危改厕工作中,拆除危房40多间,平整土地40多亩,都是您带领村民们干的,没有人找乡村干部的麻烦,是吗?——是的。 拆危改厕是一项好事,也是一项难事。您怎么做思想工作的。——慢慢来。 简单对话以后,乡贤给我介绍了几个难缠户。有一个残疾人,跛子,年纪比较大。家里五间土砖房子,快要倒塌了,就是不肯拆,又哭又闹。我天天晚上到他家,他不理我。不理,我也去。跟他说,这是国家政策,是有利老百姓的好事。一个屋场700多人都同意,你一个人不愿意,那是不通情理。三十三天,他终于不闹了,我说你这就是同意了。还有一个69岁的老女人,家里五个人,有几间瓦房,还有一座平房。三番五次做工作,就是做不通。有一次她不在家,我们把她瓦房用推土机推倒了。她回家又哭又闹。我同村干部一起去,骂我是肉头,我随她骂。说,这是大家意见。 “我头上骂起壳了!”——乡贤这话比诗还精炼!我很佩服他的创造性。 沈老不动声色地说,做这事,得罪人多。挨骂的时候有些气,现在没有气了,大家一团和气。“这事”指的是做屋长调解难题的事。一个700人的大屋场,家有千斤,主事一人,有些事推不脱。他说,一屋大人小孩见了我就re我,re,是方言,就是热情地“喊”的意思,说明大家都尊敬他,喜欢他。 依然是我问他说。讲了四个故事。 十多年前,屋里两兄弟吵架,大吵大闹,结果弟媳妇在哥哥家吊死。娘家人不让收尸,摆在家里五、六天。又是他出面,三番两次说好话,娘家人说让他哥哥来。这一次,沈互和不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出面,而是叫了屋里七、八个人一起去,怕吃皮肉之苦。不是唇枪舌战,而是软磨硬蹭,让男人说够,让女人骂够,终于让他们平安回家,终于答应装殓。人家还是看了他一点薄面子的。 五、六年前,屋里有两家人为了一座坟闹了好几年。都说是他家的,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打架、砸屋,闹到派出所,还是处理不好。没有办法,派出所领导上门请他处理。其实,他心知肚明,坟是被砸屋人家的,家谱里面说得清楚明白。但是砸屋人就是不肯承认。沈老自己掏钱,把被砸的房子整修好,砸屋的人看到屋长这样,觉得不过意,答应和好。几年的冤仇一旦化解,沈老也免除了一块心病。 久而久之,沈老的和事老出名了。高岭乡建自来水厂要拆迁一户人家的房子。乡村干部处理了三天三夜都没有处理好。这家男人有残疾,女人拿着药水瓶子到乡政府,说,要拆迁她家房子,她就死在乡政府。束手无策之际,忽然有人想起了沈互和,说女人娘家是汪冲村沈家大屋的,叫他做工作。娘家是娘家,出嫁一、二十年孩子都十五六岁,能行吗?沈互和来到这户人家,还是慢慢说,终于,沈家姑娘给沈互和面子,答应让开一条路。乡干部喜出望外。不多久,沈互和又来了,用他并不能言会道的瘪嘴,依然慢慢说。心诚所致,金石为开。女人终于答应了。沈老说,因为这件事,乡政府提名他为新乡贤。 屋长不是法人,法人是组长。也没有工资报酬,是目前中国连名份都没有的 “长”,但责任重大。平常700多人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大事小事,都找他屋长评理。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包公也有难公断的案子。但是在沈家大屋,沈互和说谁有理谁就有理。因为他是乡贤——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在700多人中有威信,有威望,德高望重的乡贤! 他的家是“乡贤之家”。家里贴有沈氏族训——祭祀不可不殷也。事亲不可不孝也。天显不可不念也。身不可不修也。持家不可不勤俭也。尊卑不可不辨也。择师不可不慎也。教子不可不严也…… 2018/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