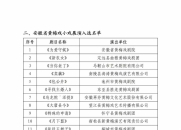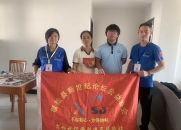|
捱时辰日子
石普水
宿松方言是一个百宝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我而言,使用它比书面语更得心应手。
正月里,我做临时保姆。孙子跟我很不配合。身体扭着,用小手推我,用脚踢我,嘴里还嚷嚷着“抗议”。类风湿的妻说我引孩子“不得法”,我承认。没经过培训而上岗,自然不是合格“保姆”。孙子家里关不住,要到外面去。外面阴雨绵绵,妻说,到哪里去?我知道哪里去?主动权在孙子手中,他哪里不闹就到哪里去。抱着孙子,我时不时地看手机上的时间。这情景用一句恰如其分的方言词语来准确表达叫“捱时辰日子”。
自然想到那种 久违了“捱时辰日子”的体验。
1967年,我在一个20多平方米的茅草屋里“打罗匮”。一块大大的石磨,一个大大的木罗匮,一头骨瘦如柴的老母牛,一个12岁的我。老母牛两眼戴着粽叶做的眼罩,鼻子串着一根固定在石磨上的竹竿,肩膀上架着轭头,极不情愿地拉着石磨一步一步转圈圈。我两眼盯着石磨里放出来的麦粉,铲到罗匮的筛子里,两手扶在两根草索系的竹竿上,两脚向两边用力踩,中间那根粗木头柱子相互撞击而发出枯燥而单调的“gan——gan diang gan”。这项工作叫“打罗匮” ,如今在中国已经绝迹了——不知有没有申请“非遗”。
我每天清早一直到傍晚,就在这20多平方米的磨坊里。我的伙伴就是一头老牛。老牛什么也看不见,我却只能透过五根窗棂望着窗户外面的一片狭小土地。公鸡在骄傲地引吭高歌,母鸡在专心致志地低头觅食。拴着的猪在不安分地大声叫唤着。摇头摆尾的狗跑来跑去,不时传来吠声。叽叽喳喳的女孩,吵吵嚷嚷的男孩,在屋前屋后追追打打。12岁的我,正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龄,无忧无虑,天真烂漫。因为 “文化大革命”,我被迫辍学回家捡粪,放牛,精明的父亲说 “打罗匮”风不吹雨不落,还比捡粪放牛工分多。
我天天被栓在这风不吹雨不打的磨坊里,望眼欲穿地看着磨盘里的麦麸筛下白粉。一道,两道,三道……一直到七道,我才解开老牛,也解放自己,加入孩子们欢乐的队伍里。
我一生中最黑暗的年月是学木匠。师傅家在黄梅县独山镇柴岭,说的是黄梅腔的宿松话。师傅黄梅人,但在宿松做事。在学校修理课桌凳时,我跟一个姓徐的本地人解锯。手里拉锯,心却飞到旁边的教室里,飞到外面孩子们的欢声笑语里。晚上回家跟师傅一个鳏夫的哥哥睡觉。有时候跟师傅到岳父母家,跟他岳父母一床睡觉。那是多么尴尬啊!我缩手缩脚——准确地说是不知所措,手脚根本不知道放在哪里好。刚刚挨着老人时,陡然一惊,赶紧触电似地缩回来就这样,胆战心惊,眼睁睁地听着男女老人们肆无忌惮地打着大呼噜而一夜无眠。第二天,又跟师傅去做木匠。
在宿松一个叫唐垅的屋里做炕房。材料都是一些坚硬无比的杂木。有一种四周都是刺的柞树,里里外外都是疙瘩。我用斧头砍,斧头砍不进去而被弹出来。没办法,我去磨斧子。斧子倒是磨得白白净净的,却并不锋利,还是砍不进去。师傅叫我刨。刨吧,要么什么也没有刨到,要么刨进去了刨子却拉不出来。
黔驴技穷。我什么也做不到。急躁,羞愧,烦恼,我头脑一片空白。出来望望天,太阳老高老高,一天还没有过去一半呢。时间怎么这么慢?我不知道这一天这么捱过去。这种困境,后来听老人们形容叫“捱时辰日子”,我觉得真的是量身定做,再恰当不过了。老人们还有一个更加形象的说法叫“驮日头过岭,㧐日头下山”。我真的觉得宿松方言丰富多彩,我们的老祖宗太聪明了。
至今我还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准确定义这些宿松方言。如果说“捱时辰日子”是形容人因为不喜欢这个事,不积极主动地对待它,而是消极被动地应付差事,得过且过所以觉得时间过去得慢。这样啰嗦不啰嗦?
其实,方言不需要特别定义,它在特殊语境里通俗易懂,这就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2019年3月27日星期三农历二月廿一(2019/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