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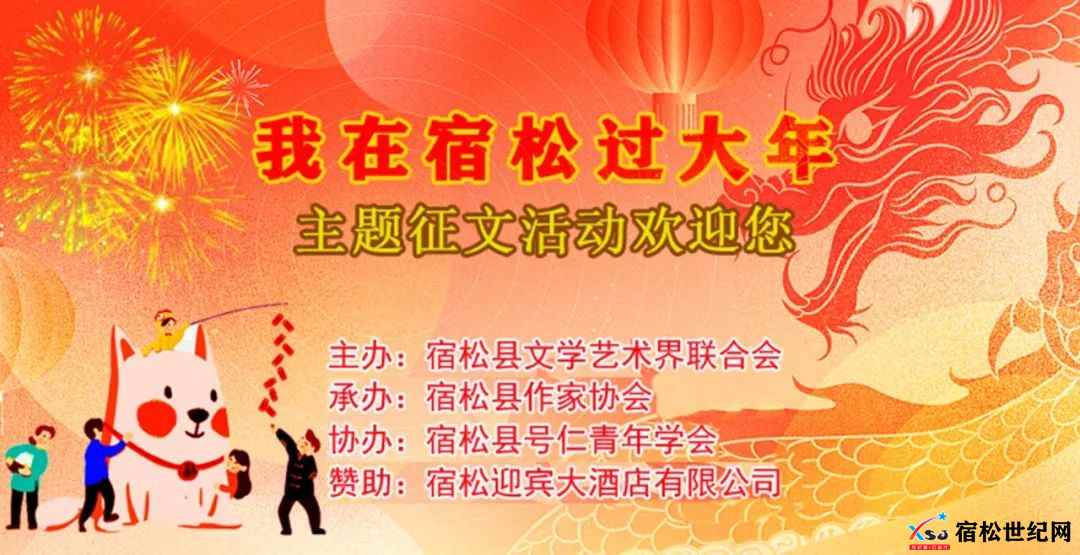
前 言
民间传说,古时候有一个叫“年”的怪兽,尖牙利齿,凶猛异常,长年深居海底,除夕才爬上岸,吞食牲畜,伤害人命。因此,每到除夕,村民们便扶老携幼,逃往深山,以躲避“年”的伤害。有一年除夕,一位白发老人来到村里,声称能将“年”兽驱走。半夜,“年”兽闯进村子,发现一户人家门上贴着红红的纸,屋里点着明亮的灯,院子里传来噼里啪啦的炸响声,“年”兽不敢往里走;待看到一位白发老人穿着红色衣服大笑着走出来时,“年”兽更是吓得浑身发抖,匆忙逃走了。第二天,村民从深山回来,发现村里安然无恙。时日一久,村民渐渐明白“年”兽害怕三样东西,即红色、火光和巨大的响声。于是,村民便在除夕贴红纸(后来演变为贴桃符或贴红对联),挂红灯笼,放鞭炮,通宵亮灯守夜等,目的就是为了赶走“年”兽。当“年”兽被赶走后,大家总是会高兴地互道:“又熬过一个'年'了。”后来,慢慢就有了“过年”的说法,也由此出现“过年”的习俗。 然而,“过年”延续到今天,却早已演变为万家灯火、亲人团聚的含义了。每到年末岁尾,当北风呼啸、万物雪藏之时,国人心中那最深沉、最温暖的情愫便会被瞬间唤醒——回家过年。这不仅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信仰,一种情感和责任。朝思暮想读幼儿园的女儿已有5岁多了,却因疫情原因一直没回过老家。听说老家冬天下大雪,除夕放鞭炮,过年杀年猪、切糖粑、磨豆腐、炸条子……寒假没开始,小朋友就吵嚷着要回老家过年。其实不仅小孩,我也一样。越临近过年,回家的欲望越是强烈,总盼望着有一天无羁无绊,开始一次说走就走的归途;总盼望着有一瞬灵魂出窍,在时钟倒转的世界里轮回。妻子虽没有我们父女俩急切的心情,却是很早就给岳父母打电话分享了回家的计划,并依次列出了诸如黑瓜子、红薯干、糯米粑、干豆粑、条子、圆子、腊鱼、腊肉等各色家乡美食,只待一回家就可以大快朵颐。人还没出发,心已在归途。朝发夕至考虑到我工作实际,妻子和女儿决定早我一周出发。妻子早早买了回家的高铁票,计划当天早上出发,晚上到家吃晚饭。没想到计划没有变化快,听妻子讲,当天高铁开到重庆与湖北接壤的地界,就飘起了大雪。看到窗外的雪花飞舞,大家开始都很激动,尤其是小孩,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但不久,高铁就走走停停,甚至一度在湖北某个站点停了4个半小时,乘客的开心慢慢就变成了焦急。然而,干着急也没有用,好在带了很多吃的,孩子们互相交换着零食,分享着储藏了一冬的故事,让大人们少了些许焦躁,也让这个冬天显得没有那么寒冷。好在平安到家,无数个家庭的担忧最终都被团聚的喜悦所遗忘。为赶上家里的年夜饭,除夕那天,我也特地请了一天假,提前买了当天早上8点的机票。从天府国际机场出发,不到两个小时,飞机就降落在了合肥新桥机场。按照计划,我乘坐机场大巴辗转来到合肥火车南站,可以赶上直达宿松东站的高铁。在大巴上,我看到合肥近年来拔地而起的高楼,快速改变的城市面貌,作为一名安徽人,发自内心感到无比骄傲。记得当年为了自考英语听力,我还于暑假期间借住初中老同学宿舍,在安徽大学住了一个月,近距离感受了安徽大学的生活与文化。二十余年的弹指一挥,合肥已一跃而成为全国前二十强城市;而我,却阴差阳错因为考研的2分之差而调剂到了离家千里之外的成都读书,故而成为了茫茫人海众多游子中的一员。可喜可贺的是,我比妻子她们幸运,虽然换乘多个交通工具,我却顺利于除夕当天下午5点钟的样子到家,和老父亲及哥嫂一家吃上了团年饭。如果你问我,“试问岭南应不好?”我学着诗人的口吻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朝花夕拾然而,从内心讲,我并不喜欢搭乘飞机的快感;相反,我更喜欢乘坐火车的从容。记得到成都读研那几年,我总是先从老家坐汽车到武汉,然后乘坐T246到成都。当时高铁少,火车票还是很紧张,也没有像现在一样可以在手机上快捷预订,我只好到了武昌站现场买,运气好能买到座位票,运气不好连站票都没有。有一年正月就没买到当天的票,只好在火车站附近旅馆住了一晚。虽然有诸多不顺,但我还是喜欢乘坐火车的感觉。看着火车在江汉平原上奔跑,继而又在秦岭山脉间穿梭,我的对未来茫然无措的焦躁心情,似乎在自然的山水切换中变得慢慢平静了些。妻子多年没有回去,除夕那天早上,就和妻弟一起回了趟她的出生地——宿松县北浴乡滑石村,一方面是想看看老家的变化,另一方面还是为了上坟祭祖,因为妻子的爷爷、奶奶和外公都于早些年过世了。其实,妻子的老家,也是我最早工作过的地方。在那个村小,我教了三年书;也正是在那期间,与妻子相识,并结识了一帮即使多年不联系也不会相忘的朋友。看到妻子手机拍的相片,那青山绿水,那弯弯的路,那镶嵌在半山腰的错落的民房,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教书的岁月:从乡上到村小,十几里山路,每次我都会花上一个半小时,走累了,就在山头的凉亭里歇息几分钟再走;冬天没有什么蔬菜,就靠校长家里拿来的一些腌菜、咸菜凑合一日三餐;课后没有什么娱乐,就靠掷石子投打一棵大树上的蜂窝来打发时间,或坐在山头苦思幂想……现在想来,还是要感谢当年的学校,感谢当年的同事,感谢当年无聊却充实的岁月,让我有鼓励,有鞭策,有走出大山的冲动和努力。从除夕到家至正月初四一早离开,我满打满算在老家吃了10余顿饭。但在家里只吃了两顿,其余都是在亲戚家转来转去,甚至在岳父母家,最后都是特意空出时间吃了个晚饭。其实,吃饭只是一个形式,并不在乎菜的多少、酒的优劣,而是家人们聚在一起,听听东家长、西家短的故事,听听兄弟姐妹们的倾诉、孩子们的成长趣事,听听父亲的牵挂、母亲的唠叨……然而,我只是善于做一个倾听者,对于家人生活的一天天变好,我也跟着开心;对于兄弟姐妹、侄儿侄女们偶尔提到的看病、上学、就业等方面的困难,却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初一下午,路过镇上以前自建的房子(多年前已出售),我情不自禁停下车去买了两袋馒头,一方面,因为那家(原来的房客)馒头确实好吃;另一方面,更是对生活在那里六七年时光的莫名怀念。路上,经过一位老同学家时,看到她正带着孩子在路边的菜地里赏花。本打算停下车打个招呼,想到她曾说过“相见不如怀念,给彼此留一份美好”的话语,还是不无遗憾不自觉就走了。自初中毕业以来,我们差不多二十五六年没见。但那时的相互欣赏、情窦初开(仅为我个人今天的臆想),应该早就被时空所消融、转化,进而变为彼此的祝福了吧,我想。其实,初中阶段我们只是学习上的互相指点、相互帮助,并没有像其他学生那般纸条传书等行为。待她到隔壁读高一时,我却因为家庭原因不得不放弃读高中的机会,转而还是在原来的初中复读准备考师范。或许,不在一个学校却给了彼此勇气,我们竟偷偷寄起了书信,当然还是相互在学习上的鼓励。一天傍晚,班主任老师把我喊到他宿舍,拿出截获的书信,语重心长地提醒我应该把心事和精力全部放到学习上来。加之母亲的过世,学习的压力,未来的茫然,我们之间短暂的故事就此搁置了下来。想到班主任,想到冬天他给我保暖的鞋子穿,想到他与我们一起点灯复习的场景,又想到他两年前被病魔无情地带走,我心中的痛楚不自主生了出来。正如: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只争朝夕在家里呆的时间不长,但对我而言,却遇到了几件趣事。——名称变了。我老家原来所在的镇名叫破凉镇,不知好久竟然更名成了华亭镇。姑且不说这个,听说我们村并没有留在华亭镇,反而因为靠近县城开发区,进而华丽转身,被纳入了龙山街道。名称一变,家里乡亲们的精气神感觉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交通变了。最有趣的是,我在老家竟然迷路了。当天开车从岳父母家出发回老家,我顺着老路自顾自地开,心里只想着赶小路快一点。谁知开到一半,一条宽阔的柏油路突兀地挡在眼前,怎么都穿不过去。我只好原路返回,怕再次走错,老实地开启了导航。不曾想原来的小乡镇,竟也让我有了如刘姥姥进大观园般的新鲜感。——环境变了。就在老家屋旁的山上,也是我小时候放牛的小山包,近几年陆续种植了1000多亩的樱花树,中间也修了很好的人行步道供游人赏花。听老父亲讲,每到四月初,各地来赏花的车子能排个几里长,卖小吃的推车也从县城、镇上争相赶过来赚快钱。其实不仅樱花树,周边有大片山头都已被流转用来栽植茶树等经济作物,姐姐们不用远走他乡也能找到很好的打工机会了。变,是唯一的不变;但故乡,还是那个故乡。附 语年没过完,我却已在路上。有人说,故乡安置不了肉身,从此有了漂泊;异乡安置不了灵魂,从此有了归途。而我说,故乡与异乡之间,只有一个“梦”的距离,只有一个“你”的相思,只有一个游子一生的放弃与追逐。(四川省成都市东部新区投资促进局 张桃荣)本期编辑:王志淮来源:宿松文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