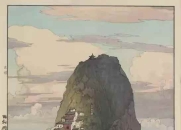|
|
|
前言 宿松是安徽文明古老县份之一,古称“松兹”,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地处长江中下游,吴头楚尾,三省交界,境内山地、丘陵、湖泊、平原依次排列,自古农渔并重,水陆通衢,商贾云集,人文荟萃。皖江文化、荆楚文化、赣江文化交相融合,禅宗文化、道家文化、妈祖文化兼收并蓄,形成了崇文尚德、勤劳创新、谦和淳朴、开放包容的地域文化品格。为努力挖掘宿松物产丰富、文化广博的地域特色文化,汲取历史人文智慧,把县委领导的工作指示落细落好落到实处,3月1日,宿松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启动“挖掘地域文化”工作,要求把散落的、杂乱的、零碎的、片断的内容有效地进行鉴别梳理、合理取舍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此基础上有集大成的新挖掘,讲清楚相关地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独特创造、价值理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多维度探索宿松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为现代化美好宿松建设贡献力量。现选登部分作品(宿松县文联挖掘“地域文化”成果之十六),希望本地人知道家乡有什么样的文化,从而更热爱家乡;期待外地人了解宿松、走进宿松、熟悉宿松、爱上宿松。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北浴乡的故事(二)——“思恩洞”的生死情缘一个地方的地名都有来历,有因家族聚居而得名,如“赵家岭”“许家岭”等;有因山水而得名,如“小隘岭”“三溪河”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关于北浴的由来,据宿松县退休教师陈殷说,北浴乡的“廖河”早先叫“西游里”,与廖河一山之隔的“北浴”,历史上称“北游里”。清道光八年(1828年)《宿松县志》《舆地志》中“山川”记载:“三溪河,距县60里。河有三支。左出罗汉荡、天马诸山,汇雾沙河,径古柳树流入;中出小隘岭、汪家山,汇上北游河,径下北游河流入;右出珠宝寨诸山,汇廖家河,径金家湾流入。皆逾20余里,同汇河口,故曰三溪河,一曰三河口。”这段文字印证了陈殷之言。由此推断,“北游”地名,“北”,指方位;“游”,指的是一条河流。“北游”之名与“三溪河”同样,因水而名。“北游”为何改成了“北浴”?不知具体原因,大概率缘之于同音相谐,年代久远,乡人以讹传讹所致。地名中同音误传的情况多有例证。据史料记载,宿松县城东侧一条南北走向的河,本名白杨河,因一河两岸遍栽白杨树而得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名白杨河改成了“白洋河”。北浴乡历史久远,动人的故事很多。如,罗汉山村的黄家山,与湖北省黄梅、蕲春毗邻,宿松县最高峰罗汉尖坐落于此。这一带群山起伏,松杉竹林连绵数十里。这里是宿松早期的革命根据地。大革命时期,县内外部分进步青年在此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群众基础,红28军和大中华抗日救国军在此开辟了远近闻名的罗汉尖革命根据地,创立了红军山林医院。这里流传着许多动人的红色故事。在罗汉尖山脚下,有一个看似普通、实则极不普通的山洞:普通,因为山洞并无独特构造,山区田少地多,山民们大量种植红薯,此类山洞冬暖夏凉,是窖藏红薯的理想场所。说极不普通,因为战火纷飞的岁月,一位新四军年轻战士曾藏身于山洞中疗伤,达3个月之久。突围负伤1946年夏,年仅19岁的湖北红安籍新四军鄂东独立二旅通讯员闵启胜,参加了惨烈的中原突围战役。独立二旅奉命掩护主力部队向西突围,在霍山、岳西、太湖等地,与敌4个旅的正规军、10多个保安团共约5万人展开生死搏斗,在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条件下,死死拖住敌人。8月中旬,闵启胜跟随部队转移至鄂皖边境太湖将军山上的桐山冲。部队来不及休整,敌人的枪声又逼近了。在边打边撤的过程中,闵启胜“挂花”了,感觉脚上一麻,一头栽倒在地上。一颗罪恶的子弹洞穿了左脚踝,脚后跟鲜血直流。他挣扎着想站起来,可几番努力都失败了,只得咬紧牙关,强忍着钻心的疼痛,顺着山势滚下山坡……同样在冲突中被打散的宿松县罗汉山村周屋籍战友吴宗贵,正好从此路过,发现了受伤的闵启胜,立即上前搭救,撕下衣服替战友包扎伤口。吴宗贵是部队的一名连长,与闵启胜并不相识。他小声告诉闵启胜:“同志,我家在宿松,离这里只有60里地,我护送你前往我家安顿,让我母亲帮你治愈伤口,再想办法回归部队。”“敌人离这个地方很近,十分危险,你不要管我,赶紧撤离!”闵启胜边说边摇头。显然,他担心吴宗贵受到拖累。“你这是什么话,我们是战友,你受伤了,我怎么能丢下不管不问呢?”吴宗贵深知,家乡一带老百姓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四军有着深厚的感情,将战友送去疗伤,最为妥帖,也最为安全。他毫不犹豫背上战友,踏上去往家乡的路程。天气炎热,山路弯弯,一路上饥餐露宿。有时身处深山老林,附近没有村落,实在饿的不行,只能摘上几个野果充饥;渴了也只能就着路边的溪流,喝上几口山泉水。途中多次遭遇国民党军队搜捕,都化险为夷,侥幸躲过。离家乡越来越近了,即将抵达老家附近的观音庵时,碰上了国民党广西军,此时天色已晚,两人赶紧俯卧在红薯地沟里。为了迷惑敌人,吴宗贵急中生智,以手捂嘴,学着野猪“呼噜、呼噜”地吼叫,愚蠢的敌人真的以为是野猪趁黑出山偷吃红薯,并没有在意。二人由此又躲过一劫。就这样,吴宗贵背着闵启胜,历经三日三夜,终于抵达老家黄家山。山洞疗伤令吴宗贵没有料到的是,黄家山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将这一带称为“匪窝”,到处可见参与“清剿”的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保安团。如此恶劣的环境,把战友安顿在自己家中已不安全,他和母亲及乡亲们反复磋商,最终决定趁天黑,偷偷将闵启胜转移到罗汉尖山脚下一个偏僻隐蔽的山洞里养伤。山洞高不过两米,洞顶呈圆拱形,底部平坦,洞内容纳一个人还得侧卧。洞口缠满蛛丝,四周茅草掩映,荆棘丛生。这个“理想”的疗伤之所,是吴宗贵母亲砍柴时发现的。为了安全,老人特意在洞口周围堆满柴禾,陌生人从此经过根本看不到洞口。生活上的事不难解决,吴宗贵母亲和乡亲们以上山砍柴为掩护,每天轮流给闵启胜送饭送水,哪家有带滋补的食品都会留给洞中伤员。最难的问题是闵启胜左脚肿胀,伤口严重发炎,急需药品消炎。山区本就缺医少药,国民党反动派又实施药品封锁,即使有钱也无处买药。情急之下,还是吴宗贵的母亲有办法,取用“陈红茶加盐水”消炎的民间验方。老人家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悉心护理,用煎煮过的盐茶水蘸上棉絮,一点点、一滴滴,帮闵启胜擦洗伤口,然后,敷上从山间采回的消炎止痛草药,再包扎好。一天又一天,老人按时擦洗换药。慈母般照料,把闵启胜感动得热泪盈眶。说来神奇,土方子果然灵验。历经3个月的精心照料,闵启胜的伤口渐渐好转,终于完全康复。隐身寺庙闵启胜待在杂草丛生的山洞中整整3个月。尽管山洞地处偏僻,相对安全,但国民党反动派隔三差五带兵搜山抓人,一旦洞口被发现,仍有生命危险。为安全起见,吴宗贵又与乡亲们商议,选派村民吴任生,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沿着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护送闵启胜转移至离黄家山不远的廖家河,在名为筲箕洞的庙宇中,当了一名出家的“和尚”。安排吴任生护送,是因为他的一个姑姑在筲箕洞庙中任居士,利用这层关系,可以照顾闵启胜的生活,保护人身安全。兵荒马乱的年月,一个来路不明的陌生人,在一个小小的破庙里住上几天,问题不大,可待的时间过长,容易被人怀疑,被坏人盯梢。小庙生活单调枯燥,闵启胜枪伤完全平复,归队心切,时间久了,也会产生烦闷情绪。吴宗贵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又想方设法,替闵启胜寻找更合适的藏身之地,还四处打听革命队伍的消息。经多方了解,得知陈汉沟老街一侧的玉枢观,四面环山,位置优越,是理想的藏身之地。尤其难得的是,观中住持常信师傅,为人正派,心地善良,在地方上享有比较高的威望。鉴此,吴宗贵托人打通关节,将闵启胜介绍到玉枢观,拜常信师傅为师,继续当“和尚”。常信师傅见闵启胜五官端庄,眉目清秀,人年轻,又机灵活泼,十分喜爱。在玉枢观,师傅白天带闵启胜去周边的方家山、鸡鸣冲、白鹤冲等地化缘,晚上教他读书识字,师徒关系愈发融洽。转眼间,已是1947年夏秋之际,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路过陈汉沟。吴宗贵获悉这一喜讯,立马拉上闵启胜一路飞奔,找到大部队,向首长详细讲述经历,申请加入革命队伍,首长同意后,闵启胜如愿回归部队,投入新的战斗。报答恩情新中国成立后,闵启胜历任湖北省新洲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等职。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进入和平年代,须臾不忘救命恩人吴宗贵,时常想念悉心照料过他的亲人,四处打听恩人下落。因时间相隔太久,仅凭自己脑海中星星点点的记忆,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慢慢查找相关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得益于相关部门的热情帮助,闵启胜终于见到了35年未曾谋面的老战友,见到了众多的乡亲们。战友相见,互致问候,抚今思昔,且悲且喜。悲的是岁月更替,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不少人已不在了,留下的只有深深的怀念;喜的是哥俩重逢,且都身体康健,可谓三生有幸。宿松县民政局王子仪,被老战友久别重逢、相拥而泣的动人场面所感染,即兴赋诗:宗贵干革命,哥俩齐参军。临危救启胜,贵留青史名。当着前来探望他的乡亲们,闵启胜立下规矩:此后无论怎么忙,每年至少来罗汉山村一次,以此报答乡亲们的救命之恩。闵启胜说到做到,年复一年来到北浴乡罗汉山村,从未间断。每次进山,都带上礼物一家一家探望,嘘寒问暖,促膝交谈,帮乡亲们查找致富信息,拓宽农副产品销路。每次到乡亲们中间,他都要重复一段话:“在革命战争时期,是罗汉山村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把我隐藏在山洞里,用土方子疗伤,挽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没有乡亲们的悉心照料,就没有我闵启胜的今天。吴宗贵同我的战友情怀,常信师傅同我的师生情谊,乡亲们与我的过命交情,我今生今世报答不完!”上世纪80年代初,柳坪乡(与罗汉山村相邻)大地村村民吴先尧,前往新洲县销售表纸,遭遇歹徒诈骗,血本无归。闵启胜得悉此事,尽心尽力,多方周旋,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帮助追回损失7000多元。闵启胜、吴宗贵两家书信不断,互通讯息,了解双方工作、生活近况。闵家孩子多,生活并不宽裕,但一家人长年省吃俭用,把从牙缝中省出来的钱源源不断寄给吴家。闵启胜深知,吴家的生活更难,急需帮助。吴宗贵去世后,生活援助仍在继续。闵启胜又出资供吴家孩子上学,直至成年。共建未来农忙季节,闵启胜把子女送到罗汉山村,帮助乡亲们干农活,减轻乡亲们因劳力不够带来的生产困难,并通过参加体力劳动,培养孩子们吃苦耐劳、踏实肯干、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精神,同时,加深孩子们与老区人民的情谊。每逢子女人生的重要节点,闵老会不失时机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在罗汉山村疗伤的难忘岁月。他反复叮嘱子女,一定要懂得感恩,只有懂得感恩,才能走得更稳更远。为了告诫子孙后代永远铭记罗汉山村乡亲们的恩德,2011年,闵启胜又一次亲临罗汉山村,特意把当年藏身疗伤的山洞取名“思恩洞”,并把从武汉制作的一块石碑运来,镶嵌在洞口,上书“思恩洞”三个醒目大字,下边刻记一段小写文字:1946年夏,新四军小战士闵启胜“中原突围”负伤后,被战友吴宗贵家人及村民救护于此洞,至伤愈归队,特立碑永志。为了鼓励罗汉山乡亲们努力奋斗,创造幸福美好生活,2015年,年逾八旬的闵老拨墨挥毫,亲笔题写“把美丽家园建设好”的赠言,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乡亲们的殷切期望和美好祝愿。“家风正则后代正。”得益于老一辈的言传身教,时至今日,闵启胜的子孙一直沿袭祖辈的足迹,与罗汉山村乡亲们频繁来往。2016年闵老去世后,他们依旧坚持每年至少来罗汉山村探访一次,一次又一次报答乡亲们的恩情。闵老的女婿施向农利用自己的设计专长,帮助罗汉山红色旅游景区义务编制全域规划,全力支持罗汉山村文旅振兴,为村民致富出谋划策。吴宗贵的孙子吴梦林在老一辈的谆谆教导下,潜心医学,成为一名乡村医生,从医30余年,继承爷爷乐善好施、助人为乐、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村里有人生病,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白天黑夜,第一时间上门问诊,每遇特困患者,出诊费分文不取。2022年8月,闵启胜的长子闵锡林(武汉市公安局退休干部)、吴宗贵的孙子吴梦林和多位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的烈士后代,聚在一起,讲述老一辈们激情燃烧、脍炙人口的革命故事,一起规划罗汉尖地区的发展蓝图,以实际行动,共建美好家园,用火红的青春,续写精彩动人的红色故事。作者简介 黄奏天,男,1954年6月生,汉族,安徽宿松人,中共党员,1983年6月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专修科,曾任教师,曾长期从事史志编研工作,曾主持清道光八年《宿松县志》点校工作,曾任宿松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来源:宿松县文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