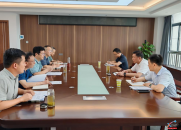|
接连几次在QQ里看到老同学屠应华发布的信息,一次是向村民宣传打扫街道卫生、保持街道整洁;另一次是拍了一张照片题名“小桥流水人家,只是有些邋遢”。心里一动,是否我也应该写点什么,向我的父老乡亲有所提示。其实在今年春节回家时就对环境颇有感触,想结合北京、三亚和吾村的情况,说说环境与健康的问题。取名“吾村与吾民”,绝对不同于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我是没有那样大的气概和胸怀的,也没有弃医从文的勇气,仅有的是那一点点的专业知识和对村民的热爱。

#自己屋后的油菜花,去年清明节回家时拍摄的。

#屠应华上传的照片,吾村村口,也是程氏祠堂门口。版权所有@屠应华。
北京的雾霾已经是举世闻名了。其实北京的雾霾由来已久,早在1998年我还在谈恋爱的时候,骑自行车看着雾蒙蒙的天,总担心这天明天还会不会“醒”来,我这想法当然是杞人忧天。那时的北京把雾霾主要归咎于北方的沙尘,其实那时候我就感觉到,沙尘是短暂的,真正的风沙来自于北京内部,到处都在“造”。到现在,沙尘暴季节没有来,沙尘就来了,我们自己还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美国使馆说这是PM2.5,于是我们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头。前几天,我开车进出北五环,真正意识到“整个北京就是一个大的停车场”的现实状况。4月29日,一个北京难得的晴好天气,我带儿子登上香山顶峰,俯瞰北京,一处处工地尘土飞扬,空气反射出暗绿色,想想自己就生活在那一片有机气体中,确实营养丰富。风水宝地的京城沦落至此,道理很简单,一个原因是超出了她的容量,无论是空气还是水,都是在竭泽而渔;另一个原因是折腾得太厉害,大城市我也见过,例如东京,没有地方象北京这样折腾,我们把这种折腾定义为发展。 工作需要我来到三亚,三亚是全国空气最好的地方。上帝简直在开玩笑,这样差别明确的对比,我想不写点什么表达一下都不好意思。当妻儿朋友在北京呼吸雾霾时,我在三亚可以享受阳光沙滩椰风。这几年三亚成了关注的焦点,很多成功人士不在三亚有一套别墅都觉得不好意思。所以这里房地产这几年是坐火箭了,越是穷乡僻壤的山野,背山或面海,越是成为开发区域,可以理解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他们非富即贵,无可厚非。一些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土著居民被拆迁了,一座座高楼或者别墅发展起来了,看看地图几乎整个海南岛的东面沿海都在开发。于是,三亚的城区也开始堵车了,海边沙滩上的垃圾也渐渐积累起来。虽然凭借大海博大的胸怀和风调雨顺、蓬勃生长的恩赐,三亚有很大的环境缓冲能力,但是我和一些朋友又开始杞人忧天了,也许10年,也许20年,三亚的空气还会那样清纯、海水还会那样湛蓝吗? 扯远了!北京和三亚与吾村有什么关系,吾村是位于大别山南麓的一个偏远的山村,距离三亚和北京各1360余公里。在我的记忆里,吾村总是青山绿水,对面山腰的雾是水雾,不是PM2.5,能滋养容颜的;房后山涧的水是能直接喝的,我就是喝那谁长大的,我用自己的身体证明了她没有什么不宜矿物质、也没有什么寄生虫;河里的水是可以洗衣服、洗凉水澡的,我小时候摸过鱼、偷偷划水挨过不少打。这样一个美丽的村庄,比我游历过的名胜古迹也差不到哪里,就是没有名气而已。我一直有一个浪漫的想法,等我老得不能再看磁共振的时候,就回到吾村,把已经倒塌的老房子用土砖再搭起来,请个村里的保姆照顾,了却余生。死后找一个松树下把骨灰散埋了,滋养一棵树,回归自然,勿需任何形式的祭奠。 记忆和现实相差越来越远。在我5岁以前的记忆里,古老的村庄都是靠山而建,从山谷里汇流而成的小溪在村庄的中心形成小河,山上大量的腐殖泥土被冲积到盆地的农田里,所以从我家谱记载到现在的400余年里,这个村庄基本自给自足。后来,我们把小河改道山脚下,这里的农田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年比一年贫瘠,到现在农田干脆都改作城镇化建设用地了。城镇化建设也没有错,毕竟从整个乡的大范围内看,把一些在偏僻山坳里的居民迁出来,更有利于他们生活的改善。形式上已经城镇化的居民,在生活方式上却脱节,这在我访问过的吾国其他地方都存在同样的问题,非吾村独有。 正月初六清晨,我被窗外的车水马龙声闹醒,外面的几辆农用车和拖拉机挤成一团互不相让,我担心堵的太长形成死结耽误我的行程,方言夹杂普通话,指挥那些一脸不明白的司机们进进退退,本想在吾村的早晨睡个懒觉也泡汤了。哥哥去世后,我是这个家的代表,母亲按照惯例把正房安排给我住,正房临街,嘈杂且灰尘重,我一直不愿意住。我更愿意住在背街的小房子,朝东,不吵不闹,清晨能看见阳光、听得楼下鸡叫。这么多年,无论我在外多么操心失眠,到这里总能睡到太阳晒屁股,或者母亲喊我吃早饭。营生需要,村民们一般选择临街的房屋。狭窄的村口,晴天漫天灰,下雨一身泥,PM2.5比北京一点都不差,这种嘈杂的环境,做生意还可以,却不适合过日子。这种嘈杂环境是一种致病因素,心理的和生理的。我担心吾民没有城里人的经济基础却有城市人的致病因素。过日子还是应该离公路和街道远些,我在美国看到,美国农民的房子很少在公路边,一般都在农场的中心,离马路有50-100米;美国的城市居民一般也住在郊区的house里,和农村一样,离马路至少有一些灌木丛隔离。只有中国人到北美后,愿意住在热闹的城市中心downtown。我们啥时能改变这个习惯,需要从文化上来解决,那是“吾国”的水平,我够不着。 河道里更没法说了。不知道从啥时开始,河道成了垃圾场。河道的滩地上堆满了垃圾,河边的灌木上也挂满了红红绿绿的塑料袋,等待发一场洪水冲走。河里的小鱼也不见了,前几年我回乡时看到有人拿电触鱼、用药水毒雨,曾经去阻止,现在也无需了,因为已经没有鱼了。现在母亲不再会因为我下河戏水打我,但是我却因为这水再也无法下河洗澡,因为上游的乡村也是这样的。和胡向明书记说到建设安徽美好乡村,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垃圾的处理问题。能否家家户户出点钱雇佣一个在家务工的村民收集处理垃圾,又担心落一个摊派的名声。水的污染是一个大问题,全国各地都在爆料地下水出问题,其实都是以前积累的恶果,吾村目前还没有化学工业,但是饮水的瓶颈已经开始出现,因为作为乡镇中心人口越来越多,纯净水资源已经捉襟见肘。村民用水各自为阵,有的在自家后院取地下水,有的引用山边的泉水。干净的饮用水是健康的根本!唯有源头活水是不够的,还要保证排放的水不污染水体才是长远所见,这一点是村民的远见达不到的。这个地方的水资源十分有限,在我的记忆中,80年代曾经有过持续的干旱,吃水要跑好远挑,等山崖下滴答的泉水聚满一担。 我的思想并没有保守到想让吾村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但是我想让吾村成为一片净土,一片可持续发展的净土,吾民健康富足、知书达理。我去过上海郊区的周庄,我想这个周庄可能当初是被发展遗忘的角落,没有被拆迁,幸运成为传统和文化的保留地。也许有一天,吾村可以成为这样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我和胡向明书记说,你担任的书记的迎宾村有幸成为建设“安徽省美好乡村”的资助对象,希望你不要象花四万亿那样,把水泥钢铁从地里挖出来又埋回去,留下一堆能耗污染的债务和通胀的恶果,引导吾民好好利用山的恩赐,做好茶叶、林业、扩展生态养殖业和农业,这些都是现代城市生活的所缺少的,将来肯定因为珍稀而大有市场,吾民的生活也就不愁。 引导吾村走自给自足的生活,似乎有回到原始的小农经济之嫌,这绝对不是我的出发点,我希望吾民的生活既有城市人的便利,又有农村人的闲适。这几年液化石油气取代了柴火,用水用电,农村的能耗增长起来,这放在“吾国”的水平是一个天文数字。其实农村的能源是能自给自足的。原来回老家连个热水澡都困难,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后,几乎能24小时热水。到三亚我看到路边的太阳能+风力路灯,我就想到,其实农村的自然环境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清洁能源,达到能源自给自足。目前国家的太阳能电池业遭遇困境,如果把市场转向农村,何苦需要欧美救市啊。我建议胡书记(胡向明书记)不要把建设美好乡村的资金花在砖砖瓦瓦上,可以花5-8万公款去日本考察学习经验,争取建立环保村、低能耗村的新概念示范村,吾民们外出打工辛苦挣的钱将来也能保值养老(只要官府不强调太阳能也是国家资源需要收费收税),减少老年的生活成本。如果有必要,我可以自费在吾村建一个示范工程,设想在山旁溪边,有一个能源自给自足的小屋,喝的是山涧泉水,有城市之便而无车马之喧,不亦乐乎!只是我现在还不到回去享受的年龄。 说到这里,想到“归隐”这个成为历史的字汇。古代有归隐制度,不管多大的官,都要致仕归隐。一个在外当官的人,归隐时都会给村民带回一些村外的见识、人脉和机会,大家到皖南旅游看到的民居,都是这些在外或官或商的人带回的。只是我们这一代,年轻的时候都以离家越远越好,大凡有点能耐的,都迁走了,吾村也就越来越萧条。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户口已经不在村里了,吾村从政策上讲已经没有我的片瓦,只剩下母亲的惦念和孩童的记忆,荣誉感也就越来越差了。 我一介医生,在外不当官发财,惦记吾村与吾民,实乃一种思乡情怀而已。
本日志是我5月1日在北京-三亚的飞机上起笔写的,写到一半刚好迎宾村的村支书胡向明和我的表弟朱仁飞来我这里,都是儿时的朋友,相聚的短短时间还是聊吾村与吾民,更加敦促我把这篇日志早日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