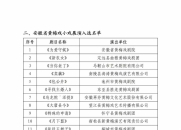|
科技与青春 宿松中学 熊文鑫
科学如青春一样,是充满活力的,但青春易逝,科学却永远不会老去。许多人不懈地去追逐科技的光芒,他们已逝的青春便又重新焕发。 重庆大学谢更新教授,出生于1971年,如今已经50岁了,然而在他身上,我看到了青春的影子。作为嫦娥四号生物科普试验载荷总设计师,谢教授向我们讲述了他的团队是如何让种子在月球发芽的。 实验选用棉花种子、油菜种子、拟南芥种子、马铃薯、酵母和果蝇卵,“生态圈”由此确定。然而团队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月球表面的温度,那个在中国古代叫做广寒宫的东西竟然那么“热”,不能实现控温,植物根本无法生长,于是他们花重金研制了一个金属盒。研发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谢教授说他们几次都面临着“归零”的危险,很多人不看好了,团队从最多的50多人减少到只有十几个人。他们没有放弃,不但实现控温,还攻克了灌溉等重大问题,最终在月球上“种”出了绿芽。 这是人类在月球上种的第棵一植株!我感到,在讲述过程中,谢教授是真的动情了。 然而,外国媒体的一些质疑和抨击也不少。“有的人会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确实,但是科学成就是有国界的”,对于那些恶意的抹杀,谢教授这样感慨。 谢教授的讲述让我产生了对在外星球种植植物的兴趣,我们是否可以把那个小金属盒扩大,种植更多,让它们繁衍呢?或者能否在月球地底腾出一块生命的空间? 谢教授能够成功,我想离不开团队,而团队应是朝气蓬勃的、团结的。 在土木土程学院建筑模型的制作是给我启示很深的活动。它让我体会到团体的重要,团队中核心精神的必要,以及严谨细致的科学品质。 在上午的制作中,我们分组起步很慢,虽然分组里我和另有两个同学同乡一起来的,但意见和分歧很多。在设计过程中一开始我对建筑数据要求把握不好,无从着手。同小组个别的同学,又一味地只说不做,我就急了,很不配合。模型大体形状确定后,由于我们刚开始采用有四个等腰梯形侧面的四棱柱框架,侧棱中斜棱的长度和接点的倾斜程度难以把握,面对激烈的讨论,我决定先算一下大致的数据,但他们没有太接受。在其它分组已开始裁木的情况下,我内心十分着急。 经过中午的休整,我思考和反思自己,觉得可能我太自信了,以至于不顾及他人的感受。然而一个高效的团队需要核心精神,既然这样我还不如埋下头来干,让这个核心精神自己出现。终于,在一次次受挫后,在志愿者哥哥的提示下,我们决定临时改变方案,把等腰梯形改为直角梯形,这样迁就于高度,我们很快搭出了框架,虽然途中几次被502胶水粘住手指,但毫无怨言。 由于前期放弃了数据测算我们的结构有略微倾斜。这就是不严谨的后果吧。无论如何,我们成功了,并且获得了组内第一。纵然有很多不快,我们战胜了自己,进一步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团结,这就好了。 有分歧,可商量,这就是青春。有曲折,可探索,这就是科技。在这个炎炎夏日,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在美丽的重庆大学,追逐着我们的科技梦。 指导老师:杨林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