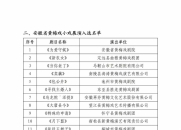|
|
许多时候,无论在晌午还是薄暮时分,无论在弄堂里还是在稻场,无论在凿得棱角分明的石凳边,还是在村口百年古桂花树下。每每你会见几个女人聚在一块,谈笑声飞扬四射,激荡在远山的松林间,石壁上,然后随着山间的清泉缓缓流淌!
他们谈论的话题大多是,年宝家儿子在外偷鸡摸狗不务正业,百亿家老人中风卧床时因为作恶多端的报应,更热门的是,把如何如男人夜间缠绵说得妖娆多姿……
听惯了她们犀利尖刻,俗不可耐的言语,看惯了她们趋炎附势,无聊做作的嘴脸,我总认为,乡村真的愚昧,也仅仅是因为那些女人。
真没想到村子里有这样一位女人,家住枫树,秋风瑟瑟之际,枫叶红的像火,柔弱女子生在枫树,濡染着枫树的秉性,生活着枫树的品格。
那年夏天,中考已过,我填好志愿回家途经枫树,一个女人在焰伯家门口,笑容可掬,热情的喊上我:“四妹,你还真不错考上花中了吧?”我不解,因为我根本不认识她。只好应付她说:“是呀,姐姐”姐姐很美,就像这盛夏时节,绽放的荷花清秀婉丽,婷婷惊艳。我是一个很少言辞的孩子,在村子总是被冷落
听到这样亲切的问候,看到那么温情笑容,我是何等的满足。这个陌生的姐姐在这个多雨的夏季,为我撑起一把油纸伞。
后来从父亲口中得知,她是家住枫树焰伯家女儿,初中没毕业就常年在外打工,前几年于归广德,怪不得我不认识。广德离宿松不远,从宿松向东南,跨长江而至。在我的理想国中,她就是宿松女儿的榜样!温情、眼神里充满关切和期许。
在高中的几年里我时常记起她,可是她回家的机会很少,周末从枫树经过回家我总会留意这位姐姐是否回宿松的娘家。
前年初春我看到父亲在菜地里小心翻土,把一想像何首乌一样臃肿的根埋进泥土里,又小心培上土我问父亲那是什么,爹说:“这是从焰伯家拿来的吊瓜秧,瓜秧是他女儿从娘家带来的,这吊瓜会像西瓜一样结子,只是个头小,可是籽粒大,粒粒饱满,没加工出售的价格也有十几……”想必,焰伯不会知道太多,仅仅听他女儿这么说,后来得知给家乡带来瓜秧的焰伯女儿是我中考那年在枫树遇上的那位陌生的姐姐。
有这样一个传说,邻村洪河一户人家的女儿嫁往先锋,可是女人红颜薄命,几年后在先锋离世,哪个女儿不想家,即使成了魂魄后,所以她总是选择在盛夏回一趟娘家,没什么可带,就带上一场及时的雷雨……
就在前年成留哥家、争留叔家、我家……都或多或少的吊瓜。
吊瓜在藕池就像宿松女儿在广德做媳妇,落根很快,生生不息,热情从容。四月底吊就上架,五月初,一边开花一边挂果,一到九月满架小红灯笼高高挂起,不是自命清高,也不是成心炫耀,这种红渗透生命本质,这种果实实而不华。在以前在今天也有许多许多的宿松女人嫁往外地,家在东至,家在岳西,更有的家在四川、上海。一开始,她们眷恋故土,一把思念的泪水洒在异地冷落后冰凉。没来得及熟悉婆婆公公就迫不及待回娘家探亲。可是一年、两年过去了,开始一家人真正过日子后发现回趟娘家路费不菲,春节回趟也感到力不从心,何况月半、中秋重阳呢,在异地只能委屈地眺望家乡。几年后她们适应了那方水土,有一天传来老妈妈病重的消息,其实是噩耗,她们迢迢千里而来,像一位不速之客操着异地方言,不见眼泪,是铁石心肠还是流尽风干?
只有这位姐姐,一个普通的宿松女儿用一种特殊的绿色生命方式保持着与宿松藕池老家的联络,瓜藤蔓蔓,牵住的是一颗思乡之心,若干年后,若干几十年后,当吊瓜蔓延宿松每一个角落,当吊瓜收入成为宿松在家务农,在家创业的人们的主要收入,当吊瓜经济成为宿松的支柱经济时,相信都会谈起这位了不起的宿松女人。
今年我发现不管水田、桑田还是说丘陵、山地都被吊瓜支起的架子连成一片。
前些日子高考回家在田间同父亲给吊瓜铺上尼龙丝网,在群山环绕的梯田里
石柱间的尼龙丝就像线谱,家乡的初夏犹如春天,线谱奏起春天的颂歌,风挟着细雨在瓜叶间掠过,弄湿父亲的额头,轻吻我的脸颊,看着在烟雨迷蒙的江南里茁壮成长的吊瓜哦,父亲想到的是秋天的收获和一家人的日子,而我想到了远在广德的姐姐——那位宿松女儿。
本文由宿松新世纪论坛坛友采集整理,来自水木清河的新浪博客——河流在宿松的大地上流淌。
|
|